第十七章 东条的梦魇
自从日军侵华开始后,由于福音传教士的长期缺乏,我们内陆教堂慈善救济工作的责任就移交到了我身上。在我的几次出行中,我不可避免地和占据在该地并不断骚扰临近地区的游击队产生接触。在五年的时光里我看见那些游击队员,在日军的暴行中孕育而成,被组织和训练成一队队的爱国者,对自己的国家和世界做着连训练有素的英国人对香港,马来群岛或新加坡都不能做到的事,做着荷兰人为了维持西印度群岛的殖民统治都不能做到的事,也做着我们在菲律宾不能做到的事。
这些装备落后的游击队,从梦想成为征服中国的人血淋淋的手上夺下他们梦寐以求的战利品。
游击活动并没有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开始进行,因为中国城镇和农村的人们普遍都善良,爱好和平和安于现状。他们能忍耐很多的虐待而不反抗。他们都愿意去相信日本发放的精美宣传信纸中所表达出的美好情感。
这个国家的人们宁愿去相信他们——直到日本人原形毕露,他们才幡然醒悟,然后开始憎恨。
刚刚在我们城市的外面,超过二十个中国女孩被捆起来绑在场地上,她们的衣服被扒光,当被给予一块遮羞的毯子时,相比自己,她们更愿意把同伴遮住。这些女孩被严加看守,强迫为每一个进入城里的侵略者服务。一个中国农夫撑着船划向那个隐藏在运河河堤下的地方,从河堤跑向他的夫人,割断捆住她的带子,然后和她一起冲向运河。两声枪响传来,这对夫妇直挺挺地掉入水里——这个国家对于日寇已经快速增长的仇恨,又吸引了另外一个村落和乡野的加入。
在中国有很多类似“利迪泽”的村落。大屠杀发生前,就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村庄被夷为平地,其中一个是“Chiao Si”,一个离我家约12000英里的城镇。在那里,日军进入后没多久,五个士兵就强奸了五名妇女。当她们一返回她们的住处,她们就被击倒并杀害了。在后面的几天,这个城镇被包围了。机枪被排列着放在街上。房子被点燃,当无助的人们跑出燃烧的房屋,每一个活着的生命都被机枪带走。“Chiao Si”被抹去了,但是在临近的村落,永不熄灭的复仇之火被点燃了。
开展活跃的游击斗争要比只有个人仇恨和对复仇的渴望更有价值。而他们的游击武装最发达的形式,就是变成整个正规军的一部分,由正规军的官员分配职责,并按照战争模式开展训练。
正是这项事业的危险和激动人心,让许多受过教育的爱国青年,也包括很多我以前的学生尤其沉迷其中。他们生活在这个国家,为他们的供给品付款,待人体贴。他们有他们的自信,尊敬和合作。他们全副武装;德国的鲁格尔手枪或是带着一只可以用来存货的木箱的毛瑟手枪,快速组装的一支短管步枪,都是司空见惯的装备。
但是大部分的游击队都被组织成地方志愿军的模式,受到正规军的训练和检阅,有时候受他们指挥。他们在他们的家乡,那个让他们饱受折磨的地方发挥着作用,在那里,熊熊燃烧的复仇之火可以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他们对于这个国家,尤其是对于国民所拥有的知识,让他们在一切游击活动中变得极其可贵。
不幸的是,当地的武装团体往往是装备简陋的,只有他们的村庄才有能力提供装备。我曾经目睹一次武器检阅,不超过五十支枪,其中四支根本不能射击,两支曾用金属丝修过,三支是中国铁匠制作的猎枪和手枪式握把的前膛枪。仅仅只有一半的枪看起来是真的能打鬼子的。然而就是这些躲在暗处的人,让日军感到危险。
那里也有一群绝望的村民,他们已一无所有,于是想在他们倒下前杀死尽可能多的敌人,在气息尚存的时候做到他们能做到的一切。有一天我曾亲眼见到过这些人扛着日本人的步枪,于是我问他们怎么得到的。其中一个人用激动的声音告诉我:
“当他们烧毁我的村庄时,我逃出去了,整夜躲在稻田的沟渠里。当他们走后我回到村庄,发现那里除了尸体和废墟外已别无他物。我在乡下流荡了好几天,找寻着我的老父母和妻儿。但是没人见过他们,他们都消失了。
“有一天我们十个人在茶馆相遇,我们商量后决定,如果我们还是个男人,我们必须为家人报仇。我们那时完全没有可以用来抗争的东西,甚至连把菜刀都没有。我们能干什么?开始复仇的唯一办法只能是从日本哨兵那搞到一把枪。铁路边有很多哨兵,如果我们同时冲向其中一个,毫无疑问他不能同时对付我们所有人。于是我们歃血而盟,在拿到枪或者被杀之前,绝不会退缩。
“第二天我们沿着运河河堤匍匐前进,穿过坟墓直到距离一个哨兵不到100码。我们等了很长的时间直到每个人都爬到不能再靠近分毫。然后我们又开始向前爬行,因为每靠近一码,就更容易成功。最后哨兵听到了声音变得紧觉起来,因此我们一跃而起并向他冲去。
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士兵,因为他杀死了我的兄弟,堂兄和我们其中的一个邻居。当我们扑向他的时候,他用他的刺刀刺伤了我们中的四个人。看看这个。”他拉上他的夹克衫,在他身体的侧面,一道六英寸长的铅色伤疤暴露在我面前。“但是我们得到了枪。从那时起,每天我们都去伏击日本哨兵,不管他们在哪,我们都能找到他们,并得到更多的枪支。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枪去阻止落伍的士兵和抢劫者进入村庄,而且每天晚上我们都去袭击沿铁道线巡逻的兵和哨兵。
游击队的名誉曾被强盗宣称的和游击队合作开展的爱国服务所玷污。虽然这些强盗是无情的,毫无人性的,对于乡野而言是灾难般的存在,但是他们的注意力往往是最有针对性的。出于最显著的经济原因,那些在占领区与日本人合作而变得富裕的中国人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当地医院很少没有几个那些被五花大绑乱枪射死,和绑在旋转烤肉架上的中国暴发户,直到他们的赃物被烧得毫无踪迹。
相比于国家的沦陷,游击战策略对限制侵略者深入后方做出了更重要的贡献。上海、南京和杭州之间由铁路和高速路围成的周长六百英里的三角地带——中国中部沦陷地区的中心。日军最高指挥部估计在那里有50000名游击队员在频繁活动,而他们从来没有能力彻底摧毁游击队。日军可以在短期内驱散他们,但却不能阻止他们在一些其他的地区重新反抗。
在宁杭公路边,另外的50000名游击队不断地突袭日本占领区,他们避免产生激战,却迫使日军在每个他们想守住的城镇驻下重兵把守。
在一次场合我目睹了游击的全过程,但是当日军要塞变得薄弱,最终的战略行动是很平常的。整个乡野都被动员了,在一个晚上城镇路两边的部分都被切开并用稻草覆盖,用泥浆把它和旁边隔离开,这些忙着逃跑或去营救的日军,被切开的口子抓住。这些被困住的日军很快就被射死。在援军到来之前这些游击队就已经跑远了,可能就跑到了援军来的地方开始袭击日军。
在1938年之后除了一些地方做了有决定的军事推进,中国的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的分界线都保持得相当稳定。日军把营房隔开三英里的距离,通过用砖头和混凝土建造碉堡等防御工事来守卫边界。一旦和平状态延续一段时间,护卫队就建造更多舒适的营房,搜刮财产,并且变得麻痹。袭击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迟早会来。如果警卫侥幸活命并逃出了碉堡,他们还是会被包围,他们所有的拥有物都会被带走或烧毁。
最终找到了放宽心的办法,但是游击队已经走了,日军认识到只有每天晚上,整个晚上都撤出碉堡才能安全些。当日军晚上撤出碉堡时,中国人就任意地穿越封锁线。破坏分子、间谍、情报员、沦陷区新招募的兵和市民进入非占领区,带着重要必需品的走私者,游击队,有时候甚至是军队,只要不引起怀疑,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穿越防线。
蓄意破坏日军的产业是中国游击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日本控制区旷野上的缫丝厂已经消失了。当棉花的收割季到来的时候,连续几周夜空都被棉花厂熊熊燃烧的可怕火光点亮。为了在成虫前把蛹杀死,蚕茧必须要加热,但因为没得到充分的加热,蜕变出的蛾通过破坏每一个蚕茧来汲取养分。但是在这发现之前,造成损失的负责人已经逃跑了。
在战前价格是十八美元一磅的顶级茶叶,在加工时并没有让它充分干燥,很快就在包装好卖给日本人的盒子里发霉了。一个燃油引擎的定时器上的小部件被拿走了,这个机器好几周不能使用,因为没有多余的部件可以更换。
在一个码头上棉花被装载上一艘平底载货船。直到拖船拉着它清扫完承重码头也没有人意识到船相对码头已严重倾斜,最终船侧翻到了河里。当事人被报道称淹死了,但是他又经常出现在别的船上,又很快地溜到其他地方搞破坏了。
轮渡过河代替了桥梁,渡船是简单的平底舟,装备着木楔来固定甲板上的汽车。到离岸几英尺处,一个拉力作用在木楔的绳子上,车子就快速地滚进了河里。我知道六个拥有这样一辆车子的人,他们是相比日本人本身,更让他们的同胞憎恶的汉奸(卖国贼)。
除了鬼子的财产遭遇不测外,他们的补给也同时不断地遭到袭击。在1940年他们位于城站的最大的仓库被烧了,损失了值一百万美刀的供应品。四十三个在那里工作的苦工被装上一辆卡车,带到寺院围墙下跪成一字,被一个日本兵一个接一个地斩首。而那个纵火的家伙在我家马路的正对面住了一个礼拜,除了日本人,每一个人看起来都知道是他干的。
破坏通信是游击队最拿手的好戏。他们的诡计多种多样,小到散布小铁机关(一种能扎破轮胎的神器),大到让火车发生事故。在1941年的十月,我乘坐的火车出事了。幸运的是我们乘客当时的时速不超过四十英里每小时。伴着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隆声,一颗地雷似乎在我座位的正下方爆炸了。紧接着一个巨大的颠簸把乘客从座位上头朝前地扔了出去,叠罗汉般叠在过道上。车厢向侧面飞出轨道,尾部的重车厢直接摔成了残骸,到处都是碎木头和玻璃。钢连廊扭曲和塌陷成手风琴的样子。这些谨慎的日本守卫一站起来,就冲出去在附近的坟墓上架起机枪对着桑葚林,仔细搜寻着有人藏着的迹象,即使是一只拍打翅膀的喜鹊也会引发他们的一阵扫射。他们知道是游击队干的好事,因为悲伤的经历已经教会他们这不过是游击队的一次袭击。出于恐惧,我曾在窗前仔细注意着乡下活动的迹象。万一发生交火,我准备在火车的另一端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所有我看到的,是三个男人把身子俯得很低,从一个大坟墓边跑出来。在那里我最终找到的却是一个带有一根通向矿坑的电线的电池。
当火车将要离开城站时,两个傀儡官员在盛大的典礼和深鞠躬中登上了火车。那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事故发生后,当这些人刚贴在一起,就又被撞倒在过道上,并被扔到我旁边的地板上。他们卑贱地因为恐惧而趴在地上,浮花锦缎沾满被打翻的痰盂所倒出的污秽物。其中一个尝试着去鼓励另一个人,但他却结结巴巴说不出话;第二个人试着去回答,但他却只能流口水。我邀请他们坐到我分享给他们的座位上,他们小心翼翼地用手和膝盖支撑着爬起来,并抬起头直到能看见窗外的景象。正当他们刚好抬起头时,日本兵在窗外开始了第一轮的机枪扫射。他们恐惧地剧烈颤抖着,并且再一次掉到了地板上。他们深知是游击队把他们的火车推进这个危险的处境,而且这并没有令人愉悦的前景。
这列价值成千上万美元的火车,包括一个珍贵的火车头,被摧毁了;交通中断了一星期;生命失去了;警卫的彻底无能得到了证实;通过三个人几小时的工作,叛徒们就得到了一次严肃、令人恐惧的警告。
所有开往平原上重要城市或南京的巴士、货运卡车和军队,都要在车队护送下才能出发。为了修路或驱散游击队而造成大约两周的延误司空见惯。埋伏变得如此频繁以至于为了避免被伏击,沿路好几英里的松树林和竹林都被从砍到只有三分之一英里了。当护送队穿过深深的峡谷时,山上的石头落下来,把货物和护送队的联系切断,游击队像捕食般俘虏或烧掉这些货物。在燃烧的货物下,涵洞破碎并坍塌了,混凝土受热也变得脆弱。运河河堤被切开,河水从一个地方排到另一个地方。
像很多其他的政府建筑一样,这条新造的横跨杭州钱塘江的长一英里的铁路、公路两用大桥在中国军队撤退时被炸毁了。桥上十四分之五的路程被扔进了河里。三年后日本建造了一座部分由是浸在水里的钢筋构成的木质桥,可以让卡车通过。但是在夜色掩护下船只的反复攻击、通过游泳者推到卡车前的水雷和岸上的游击队对日军持续造成了的骚扰。他们在岸上到处修建了碉堡,然后在桥上设立了四个警卫站来维持对桥持续的控制,然后向上游四英里内设立哨兵站,最后将码头用坚硬沉重的木料围住,来防止水雷进入。
1500英里长的长江上所有的浮标都被除掉了,偷偷地换上了放在不同位置的新的浮标。灯塔被破坏了,信号浮标被改变了方向,船只被引到礁石滩上搁浅。接着悲哀降临在那些发现自己搁浅在岸边的敌方船员上,因为游击队埋伏着等他们和他们的货物很久了。
日本为了开办新企业做了巨大的努力。一条公交线路被安排在杭州和临近的城镇运行。这很有用并且变得受欢迎。没什么不好的事发生,因此为了能多赚几个乘客的钱,军警就不被安排在车上浪费空间了。但这就是和平的终结。一天一个游击队员走到马路中间挥舞着枪。如果司机停下车,乘客就会被搜身,他们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就会被当做乘坐日本人的车而交的罚款拿走。那些对罪证着迷的人会引发更进一步的问题;农民将会被警告,公交车会被烧毁。所以司机不停车了。他猛踩油门。以一百码的速度冲向路面下埋有地雷的公路,冲向天国。
在运河河内行驶的船只也遭到了相似的命运。即使是有摩托艇的护送,也不能让他们免受从桥上扔下的,或从河道狭窄地段的河堤上扔过来的炸弹的袭击。虽然对乘客的行李有严格的搜查,炸弹还是会被携带上船。它们被藏在货物里或码头上的燃料仓里;有时炸弹会被狡黠的仆人巧妙地藏在警卫装备上的某个地方,让警卫自己带上船。为了阻止游击队这种行为,一天我看见日本人把二十箱,每箱重四十吨的柴火通通卸了下来。
日本人做宣传工作时非常聪明。我认识一个每天下午从事于分发这些宣传材料的中国人。有一天我问他会不会为自己感到羞愧。
“不会的”,他说。“你看,我每天下午把这些贴在墙上并得到报酬。我通过这样养活自己。然后我在晚上又把它们撕掉,这才是我真正的工作。”他在做他份内的事,很明确这种事情被认为是有效的地下反对行动。
我的首席助理有一天告诉我一个有趣的故事。樵夫们出现在他家的坟场,并砍倒了一棵荫蔽他家先灵住处的古树。他没有能力阻止他们,因为这些人为要把古树卖给日本人的汉奸承包人工作。过了一会儿一个经过的路人为了打发时光,仔细端详了篱笆一天,问了很多切实际的问题,正如中国人一定会做的,然后他说他有一些树在处理,并想见到承包人。他们在附近的寺庙里见面。苦力们离开了承包人,这个路人在议价。故事的最后承包人还活着。这桩生意他没有付钱给日本人。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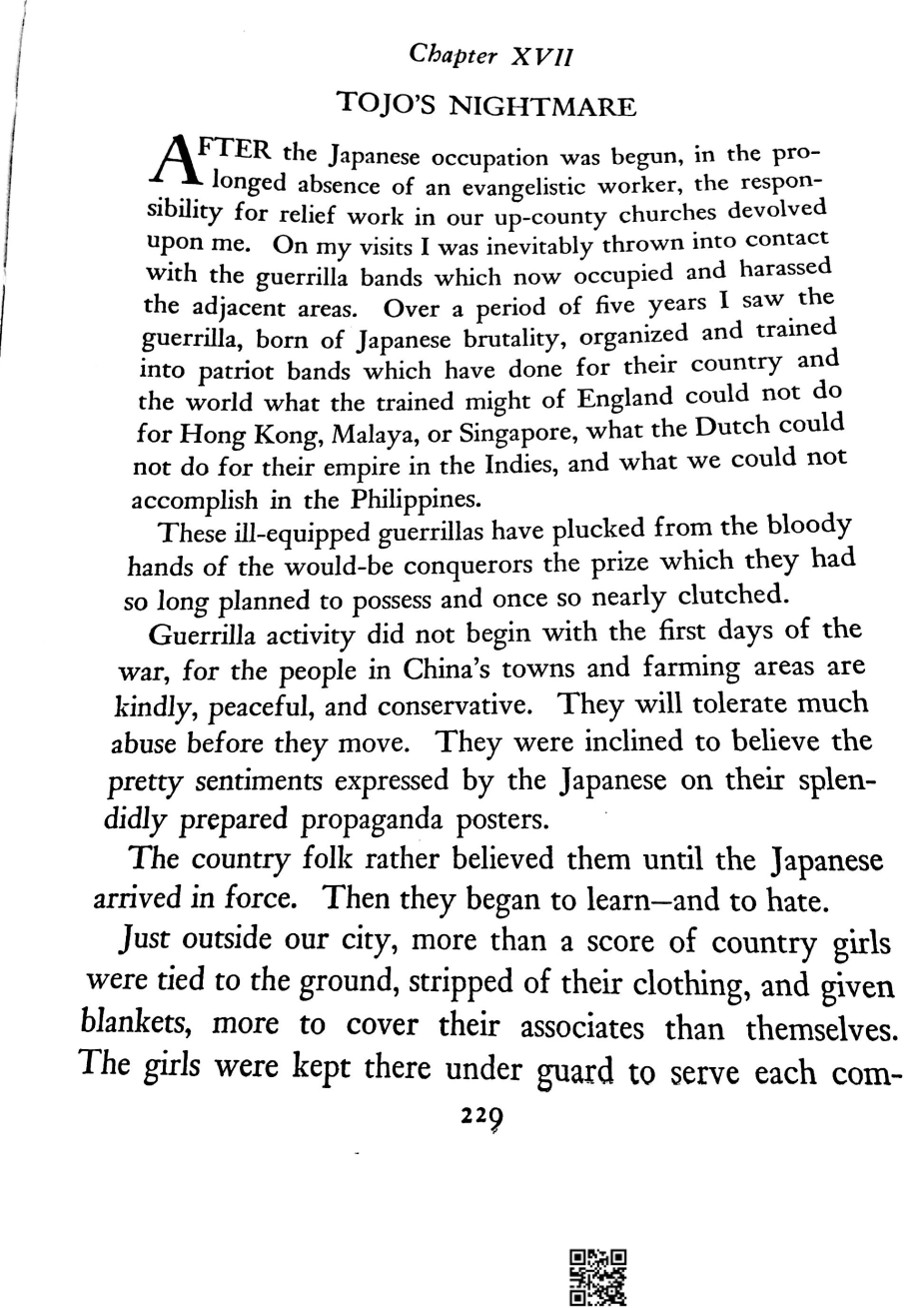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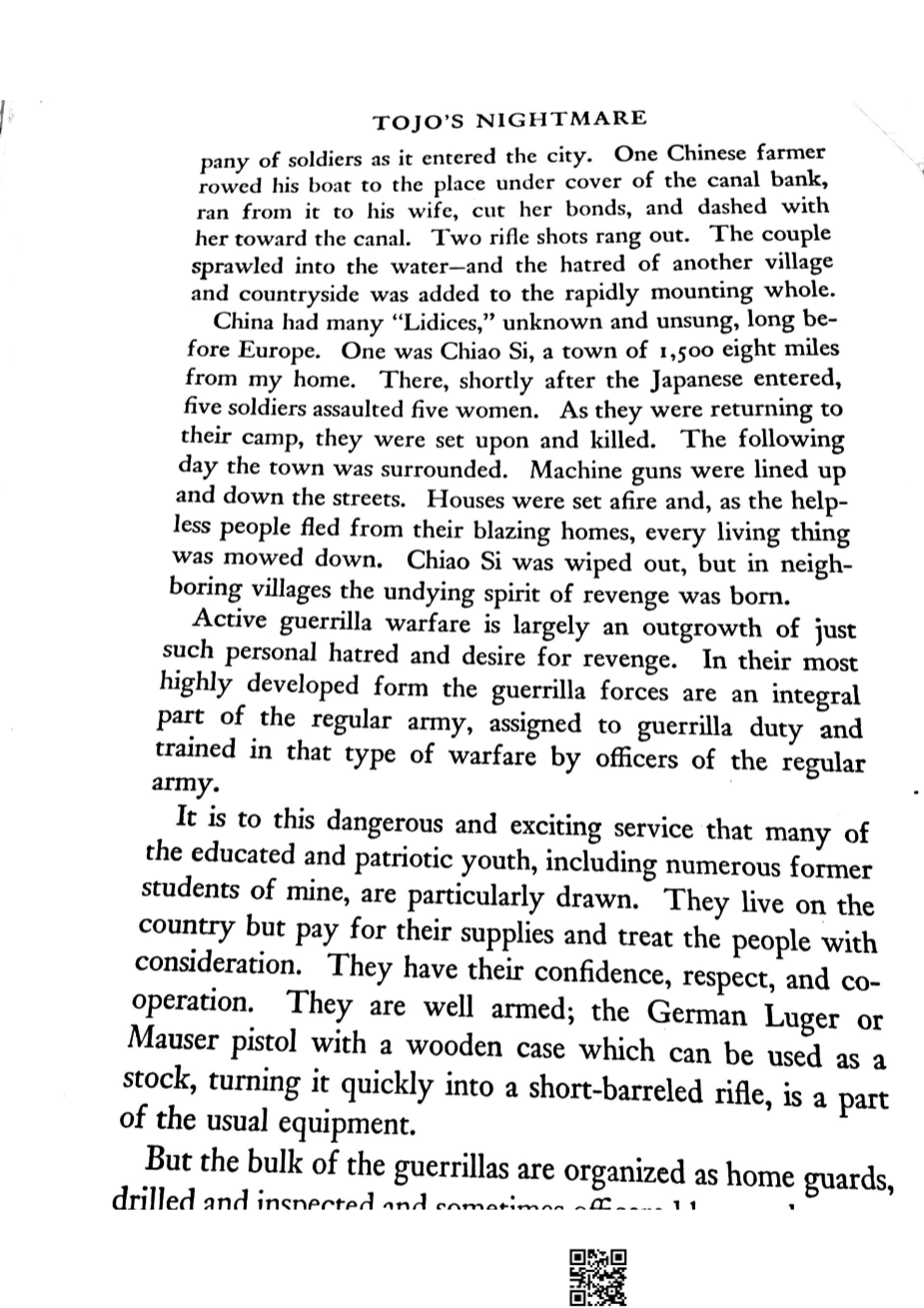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12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79287],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