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
c . Smorynski
在世纪之交,数学领域有很多哲学活动——弗雷格和希尔伯特争论定义的本质,罗素和怀特黑德试图为所有的数学建立一个普遍的基础,布劳威尔写了一篇关于神秘主义及其对数学基础的影响的论文。20世纪20年代,布劳威尔成为数学领域的领军哲学家,并成为希尔伯特的助手赫尔曼·威尔的门徒。希尔伯特意识到一个挑战,尝试了一种反哲学,并制定了一个计划,如果成功完成了这个计划,就会摧毁对布劳威尔哲学的需求,因此,这是哲学。我们都知道,库尔特·G6del并没有摧毁布劳威尔的哲学,而是摧毁了希尔伯特的哲学及其纲领。接下来发生的是hellip;,什么都没有。在由此产生的竞争真空中,布劳威尔的哲学本应占据主导地位。相反,数学家们忽视了哲学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不喜欢布劳威尔的直觉主义,也不受基金会遇到的大困难的影响。~哲学家们非常喜欢G6del的作品,并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对新的数学产生兴趣,数学哲学在大基础的讨论中停滞不的。无论如何,数学哲学直到1931年以后才有了进展。这门学科失去了它的领导地位,几乎不复存在:甚至最近的报告也将数学逻辑主义(弗雷格、罗素)、直觉主义(布劳威尔)、形式主义(可能是伯奈斯,但希尔伯特经常为此而受到指责)和柏拉图主义(官方称“不存在”)列为主要哲学。
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即将改变。目前的数学状况,让人想起发生在巴别塔的建筑师和石匠身上的事情,让许多数学家感到不安,他们试图对这种情况做出一些解释。这些尝试各不相同:一篇文章将数学定义为抽象的艺术,并以抽象为荣;有一本书宣称数学已经失去了方向感,特别痛惜抽象的倾向;许多文章陶醉于数学的多样性和它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速度,同时假设数学的相互联系和连贯,以便让任何需要保证的人(作者自己?)放心,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如今,人们对数学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至少,关于这一主题的新书层出不穷,而非历史学家正在从数学图书馆借阅这些书。此外,还有林恩·阿瑟·斯蒂恩编辑的《今日数学》、菲利普·j·戴维斯和鲁本·赫什的《数学经验》、道格拉斯·霍夫斯塔德的《哥德尔、埃舍尔和巴赫》以及《数学》;莫里斯·克莱恩的《确定性的丧失》不仅在通常没有多少数学书籍的书店里有售,而且它们的销量甚至足以证明平装本是合理的。这一切本质上都是哲学活动;它可能不是一个非常高的级别,但它确实存在。
我对怀尔德的新书感到相当兴奋。对历史的兴趣增加了,尽管它很重要,但基本上是亚哲学的,或者不那么令人讨厌的,是前哲学的。我最近读到的大多数文章都是哲学的,但总体上都是不成熟的:它们只不过是在寻找方向;他们的作者没有特定的方向——他们也不可能:他们是一个50年来没有任何领导的领域的新人。怀尔德将数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的观点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第一个成熟的数学哲学。
在讨论怀尔德的哲学之前,让我先抛开竞争。我们完全可以忽略维特根斯坦。他的《论数学基础》完全与数学无关;他是一种语言哲学,在数学家使用数字词的情况下,他对数学的影响是有限的
数学不是科学的全部;它甚至可能不是科学的一部分,但可能是与科学平行的东西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假设”——拉卡托斯的主要哲学是科学哲学(或者更确切地说:科学研究),而不是数学哲学。数学不是科学的全部;它甚至可能不是科学的一部分,但可能是与科学平行的东西。无论情况如何,事实是,自从柏拉图愤怒于阿基塔斯和尤多克索斯试图将机械考虑引入几何学以来,数学已经,而且一直拥有它相对于科学的独特地位。数学有其独特的问题,仅仅把数学哲学专门化是无法分析一般的科学到特殊的科学。虽然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为类似的数学哲学的开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但它不能提供数学哲学本身,而且这些开端也还只是一种原始的状态。此外,拉卡托斯坚决否认数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区别。他的著作《校样与驳斥》(另一本平装本的畅销书)试图证明这一点。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否定:数学比任何一门科学都更像是一个知识的累积体,也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活动,由于它拒绝面对这一点,拉卡托斯的哲学并不完美。
怀尔德的哲学 数学是一种文化体系
王尔德的哲学是:数学是一种文化系统。数学知识是文化传统,数学活动是社会性的。人们可以通过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数学家和数学。例如,存在着支配文化系统的普遍规律,这些规律也可以应用于数学文化系统。王尔德的哲学听起来不太有前途——至少不是我刚才描述的那样。但这似乎是有效的。这是有道理的。此外,当我们反思它时,它不是变得不比范畴理论所基于的想法更牵强吗?范畴理论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忽略群体本身,只看箭头所代表的“社会互动”来理解群体的某些东西?
意识到数学具有文化性质并不新奇,但很少有思想是新奇的。正如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在其戏剧版《道林·格雷》(Dorian Gray)的序言中所指出的,想法比比皆是;他们的执行才是最重要的。当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提出数学是多元的,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数学这一观点时,他并没有将这一主题发展成数学哲学,也没有试图对数学的未来发表任何看法,这一观点被许多后来的历史学家忽略了。例如,埃里克·坦普尔·贝尔在写《数学的发展》时完全忽视了这种可能性,在这本书中,他带着现代西方的偏见,反复误判了早期文化中的数学——毕达哥拉斯学派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没有脱离当时盛行的神秘主义,穆斯林把他们的实用数学建立在他们自己文化的需要上,而不是建立在温和的希腊文化的投机冲动上,等等。
让我们来看看这三个比喻:男人,贝尔,斯宾格勒和怀尔德。对贝尔来说,数学是一条“活的溪流”,偶尔有小支流,也有一些死水。对他来说,穆斯林的数学在这条河上是一个缓慢的地方,一个对保存水有用的大坝,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麻烦。而中国的数学,在其基础被西方重新发现很久之后才进入动态流,几乎不值一提。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我没看过)叫做《毕达哥拉斯是中国人吗?》会被认为完全是白费力气。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数学,数学随着文化而消失。
在斯宾格勒看来,文化是像人一样的有机体;他们经历了从年轻活力到衰亡的特定发展阶段。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数学,数学随着文化而消失。在希腊人之后,在穆斯林的统治下,数学呈现出一种不同的风格,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不同的数学:希腊数学一直是一种休闲阶层的抽象和思辩活动;穆斯林数学是游牧民族后代的一种具体而实际的活动,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严酷环境的影响。斯宾格勒永远不会犯贝尔那样的错误,谴责穆斯林没有简单地延续希腊传统。他对毕达哥拉斯是中国人的态度如何?也许他会想,为什么人们会担心将中国数学与希腊数学进行比较;当然,他会发现这个引人注目的标题背后的严重问题考虑欠妥。那怀尔德的呢?
怀尔德认为文化,比如说数学文化,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物种。这其实不是一个比喻;但有一个显然符合我们的目的。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比如古典希腊文化或现代西方文化,是一个经历一定阶段的有机体,而怀尔德则认为文化,比如数学文化,是一个进化的物种。在他看来,希腊数学并没有随着穆斯林数学的诞生而消亡,而是数学从希腊人传到了穆斯林,并在不同文化力量的影响下,改变了它的发展过程,即适应了新的环境,沿着新的路线发展。和斯宾格勒一样,怀尔德对贝尔的错误免疫;此外,与斯宾格勒不同,如果他愿意,他能够讨论这种关系。
我应该强调的是,斯宾格勒和怀尔德使用“文化”一词的意义不同。我不打算在这里给这些感觉下定义。
希腊和穆斯林数学之间的差异:他的分析更加复杂。我最好不要描述他对毕达哥拉斯是中国人吗?——我有更重要的话要告诉他。
正如我前面所说,王尔德提出了一种成熟的哲学。这不仅仅是一个顺带引用的可爱比喻,而是一个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发展起来的社会数学世界观。他有时间发展和检验这个概念,看看它解释事物的范围有多广,解释得有多好,并得出一些结论。我们应该考虑他的观点所提供的一些解释。在此过程中,我将首先讨论怀尔德给出的几个例子,然后以我自己的一种推测来展开讨论。
怀尔德很好地解释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多重发现——牛顿和莱布尼茨分别发现了微积分,诺维科夫和布恩分别证明了群体的应用题不可解,等等。这样的倍数很少。
数学家是社会生物,他们研究的问题被潜在的数学文化认为是重要的。
举个例子,如果你做了足够多的尝试,你就会得到,比如说,连续投掷5次正面。但倍数是相当频繁的,“随机巧合”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它们。然而,根据怀尔德的说法,它们是很自然的:数学家是社会生物,研究被潜在的数学文化认为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有文化力量决定某些问题的解决。他说,考虑到能力和文化力量的相当均匀的分布,促使几个人处理相同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同时解决是可以预料的。
这种解释相当平淡无奇。像优先级冲突这样强烈而有趣的事情,应该需要一个更深层的理由来回避;目前的理由表面上是肤浅的,这使得相互竞争的索赔方显得狭隘和不成熟。但他们是不成熟的:16世纪的许多关于优先级的争论,以及17世纪关于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大争论都是可以原谅的——那个时代的信息流动不是太不稳定;今天,我们很容易认识到多次复制是常见的现象,应该愿意接受一个更简单的解释,而不是普遍存在的心灵感应剽窃。
王尔德的观点还有一个更平淡无奇的应用,那就是他对数学在科学领域的适用性的解释:数学是一个文化系统,就像物理、化学等一样。如果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所研究的问题是由他们各自亚文化的文化力量强加给他们的,如果数学家和科学家之间有足够多的接触(这是肯定存在的),然后,可以预期数学将适用于科学(因为它肯定是)。
这种解释可能并不多,但比起对“数学的不可理喻的有效性”感到惊讶,这是一种进步。对于那些想要独立于人类载体之外的科学和数学解释的人来说,这是不太令人满意的,例如,肯定宇宙在结构上是数学的,否认我们强加给它一个数学结构。有些人也很沮丧地意识到,随着数学分裂成脱节的群体——现在大学里有独立的纯数学、应用数学、统计学、运筹学和计算机科学系——以及数学家和科学家越来越分离,未来的数学对科学的影响可能很小或根本没有。例如,Kline对这种可能性反应强烈,在数学中;《确定性的丧失》要求停止纯数学,回归科学。7 Grsquo;
如果我们接受关于数学在科学领域的适用性的社会解释,我们也接受数学家正与科学家渐行渐远的假设,那么我们确实可以预见到,未来的某些数学对科学领域将不会很有用。面对预测,人们可能会张开双臂、泰然自若、难以置信或惊慌失措;他们可能会得到规范的回应——比如克莱恩危言耸听的禁令。怀尔德平静地看待形势。也许他只是没有得出明显的结论,或者,也许他已经预见到一种抵消的力量来阻止结论所描述的效果。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数学中不同分支的合并发生了赋予数学内在的统一性。但在他看来,这些巩固是社会力量的结果,依赖于文化拒绝分裂自身。一旦分裂发生,如果我们使用达尔文的比喻,新的独立的亚文化可能进化成不同的物种,不能交叉受精。当然,有一些文化力量在对抗分裂:Kline就是一个例子。甚至还记得勒贝斯-格对《基本数学》编辑的警告:专业期刊不可能长期保持高标准。但是,如果有反对分裂的力量,就会有支持分裂的力量:个人除了有机会了解一篇偶尔发表的文章之外,几乎无法订阅任何专业期刊;对新颖性和研究性的强调不利于学术;数学和科学的民主化迫使(不仅是允许)初级教师独立工作,而不是作为经验丰富的大师的助手工作几年,这些大师可能被认为在自己的领域有更广阔的视角。怀尔德可能认为反对分裂的力量会获胜——他没有说;我打赌这些军队会的输。
我似乎有点偏离了轨道;但我想这只是表面现象。正如拉卡托斯所说,“一个给定的事实只有在一个新的事实也被它解释的情况下才能被科学地解释。”一种解释的价值,无论是哲学理论还是科学理论,不在于它解释已知事实的能力,而在于它预测新事实的能力。我们必须将王尔德的观点推向极致,以检验其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看看我们能做出什么样的预测。我,在智力上有点保守,只会做出最温和的预测,也会通过明确说明我的额外假设来对冲我的赌注:我预测,数学哲学和数学历史将在未来几十年经历重大发展。这两门学科甚至会在数学界获得受人尊敬的地位。
正如我所说的,我只是做了一个温和的预测:人们对哲学和历史问题的兴趣增加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已经有好几年了);我只是说,这个运动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它背后的推动力是如此强大,事实上,即使是如今通常只重视复杂数学的数学家,9也会认为这些活动是合理的。
我的预测背后的假设是当前人们对哲学和历史重新产生兴趣的根本原因是数学家中存在的一种“碉堡心态”。为了说明支配文化的一般规律的存在,怀尔德引用了人类学家h·l·夏皮罗(在怀尔德的意译中)的一项观察:“一个民族或文化对军事上和数字上更强大的民族长期严重压迫的反应通常符合一种经典模式,即传统宗教的强烈复兴。”现在,数学亚文化并没有受到严重压制;但数学家们确实觉得他们已经失去了控制:没有人理解整个领域(参考上文引用的戴维斯和赫什的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好的讨论);资金来源正在枯竭——数学不再吸引最优秀的学生(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一些对数学友好的人公开“承认”这门学科已经发展起来了;数学的竞争对手TM对数学进行了卑鄙的攻击,有时甚至是在公共场合。现代数学家并没有受到压迫,而是被围攻,他感到自己是这样,并公开对此表示惋惜”——这就是我提到的掩体心理。应用怀尔德的哲学和沙普罗的观察,我们可以预测——虽然不是回归宗教,因为数学没有宗教2——相应的内省依附于传统,即对数学哲学和数学史的一种情感兴趣。
还有其他的文化原因可以预测哲学和数学历史的持续发展人们甚至可以在威尔德的书中找到它们;但这些理由并不一定支持我所预期的增长幅度,因此我将不再进一步讨论我的适度预测的合理性。。相反,我将尝试用社会术语为潜在的数学哲学家提出建议,以增强这种预测。l*怀尔德自己也提供了一个附录,是关于对有抱负的数学家的建议,但这个建议相当宽泛;我将尽量讲得相当具体。
1.的地位。不用说,地位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数学哲学家要想被数学家所接受,不仅要精通数学,而且还必须是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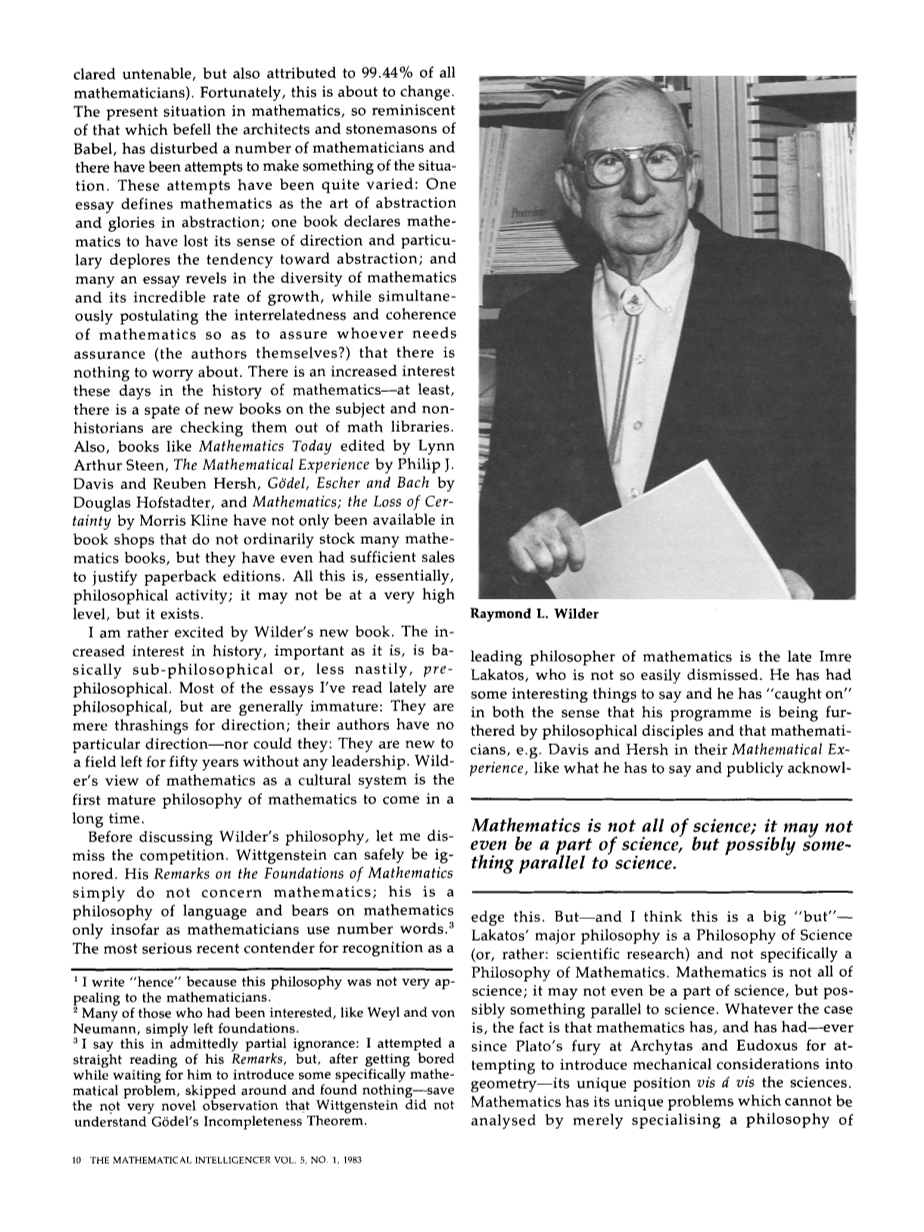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7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593021],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