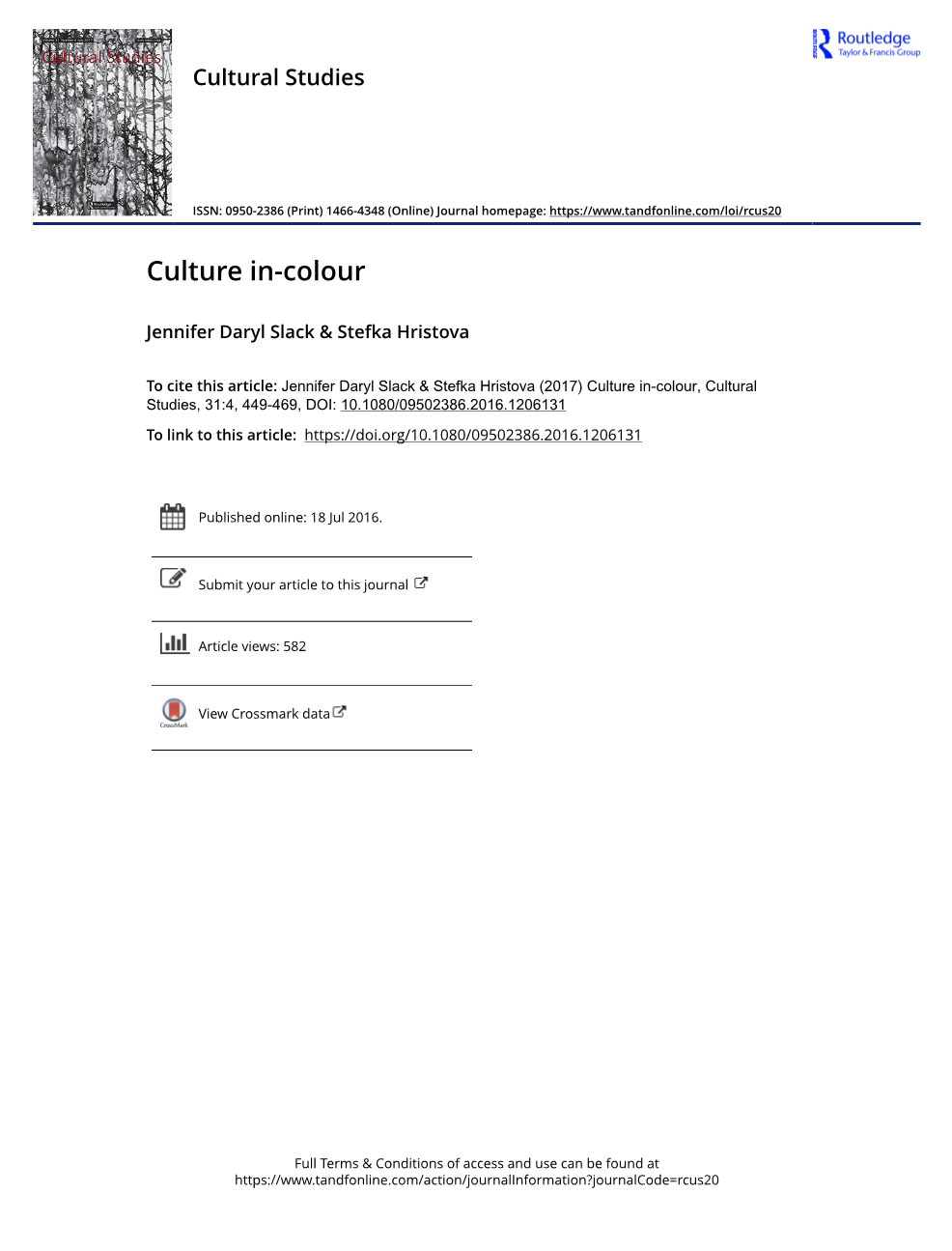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22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色彩文化
达里尔&珍妮佛 斯蒂夫卡里斯多娃
密歇根理工大学人文系,美国密歇根州霍顿市
摘要:
颜色中的文化是一种概念,它承认某种文化总是在颜色的形式、结构或系统以及颜色的关系中共同构成。这两种制度——颜色和颜色——相互折叠并相互渗透,形成复杂、多元、矛盾、结构性的文化关系,这些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将色彩文化理论化是基于并超越了电子人的形象来坚持色彩,它既不是一个事物,一个物体的属性,也不是一个神经过程,而是一个活跃的动词,一个活生生的事件:中间和发音,重复,斗争,重新组合,和形成。这条裙子是2015年在互联网上流传的一个关于服装颜色的争议,它揭示了色彩是如何被典型地认为的——表面、艺术和装饰;科学事实;以及神经现象——以及它是如何被情感地生活的。这件连衣裙所产生的焦虑暗示了一种张力,即对颜色如何重要的典型解释与对颜色和颜色都重要的不易接近但更重要的方式之间的张力。颜色和颜色通常被用来表示社区归属,但仔细观察不同颜色的感知威胁,就会发现在颜色是什么以及颜色的可靠性方面存在潜在的信任,从而在包容、排斥和等级关系中协商/构成社区。神经科学和技术解释通过断言颜色的稀疏性和相同性,以及通过消除颜色的有力的清晰度工作的痕迹来有效地控制颜色。然而,正是色彩系统本身,才有可能摒弃色彩的显著性。认识到我们生活在色彩中,不仅需要认识到我们生活在色彩中,而且还需要认识到不同的色彩文化是可能的,不同的色彩形式或系统是有情感地生活的,并且颜色的纪律可以被抵制,其效果更容易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
关键词颜色;颜色;在颜色;社区;服装;网络记忆;影响
在色彩上可以找到和声、旋律和对位。(查尔斯·波德莱尔1956)颜色是不可持续的。它毫不费力地揭示了语言的局限性,并逃避了我们对它施加理性秩序的最佳尝试。(巴奇勒1999)
1.它是或不是关于一件衣服
Adress于2015年2月27日点燃了社交媒体。不是随便的,而是衣服的颜色。关于婚纱颜色的争议始于母女之间的争议:Cecilia Bleasdale给女儿Grace发了一张她打算在Grace婚礼上穿的婚纱照片(Bleasdale 2015)。塞西莉亚看到这件衣服是蓝色和黑色的,而她的女儿,看着这张照片,看到的是白色和金色。在家庭纠纷中,这件衣服的颜色很重要,因为在西方文化中,在婚礼的背景下,白色是专为新娘保留的。当21岁的婚礼歌手凯特琳·麦克尼尔(Caitlin McNeill)在社交媒体Tumblr页面上发布了这件连衣裙的照片时,这场辩论变得公开化,并引起了广泛关注(Knapton 2015)。这就是两人如何看待“网上办公”服装的颜色的简单区别(兰道和西尔弗斯坦,2015年,哈里森,2015年)。对于那些在未来几天内受到媒体广泛报道的人来说,要避免在发行过程中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是:衣服是蓝色和黑色的,还是白色和金色的?观众对这件衣服的颜色既有把握又有分歧,他们大声呼喊着对其颜色归属的忠诚。美联社的一篇文章(Pogatchnik 2015)称,“辩论激烈”;“争论hellip;hellip;烧毁了互联网”(Landau和Silverstein 2015);一位推特用户称之为“蓝黑金白战争”(@Mindykaling 2015)。八个月后,争论仍然没有定论,因为这件衣服变成了一件万圣节服装,让人想起了杰基尔和海德:一半是白色和金色,一半是黑色和蓝色。所有关于服装颜色的争论?
虽然激情病毒活动在社交媒体上很常见,但偶尔也会在印刷和广播中报道,正如这一争议一样,这一分歧显示出一个不寻常的特征。除了典型的(到目前为止是一般的)判断和尖刻的直指那些表达不同立场的人之外,这件有争议的衣服的颜色也引起了不适的内倾。人们感到困惑和怀疑他们的确定感。他们都“用自己的眼睛”捍卫和不信任他们所看到的。他们甚至——可能有点开玩笑地——质疑自己的理智。《纽约每日新闻》(Landau and Silverstein 2015)报道的推文包括:“我很困惑和害怕(@Taylorswift13)”,“我这么做是在给我施加压力(@Chelseykwok)”和“我在窃听(@Joeysalads)”。《大西洋》(Garber 2015)报道说,“它使我们其他人质疑我们的理智、朋友和现实的本质。”
对这种令人不安的差异有一种解释,而“通常的嫌疑犯”则表现出一种平静人们不安的样子:我们甚至在相同的情况下,对颜色的命名也不同;神经系统的差异450 J.D.Slack和S.Hristov考虑到看到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显示器显示或环境光反射颜色不同;以及颜色无关的断言。然而,伴随着这种对解释的探索,颜色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有趣。这件衣服表明,我们相信颜色既可以作为一种形式、结构或系统(我们称之为颜色),也可以作为文化意义(通过颜色)的可靠提供者。那么,如果颜色被不确定所笼罩,我们就不安了。因为在一个非常真实的方面,我们总是在色彩(我们把这个术语作为我们探索的任务)和文化总是在色彩,我们对色彩的信任是一致的,在文化中作为已知的东西,在我们的意义上我们在它的位置。当色彩变得不可信时,它会威胁到确定感、自我意识、适当关系的不和谐感,以及对文化整体的信心。当对文化的信任被破坏时,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生活中的色彩。这件衣服还表明文化与颜色或颜色的特殊关系不是囚禁。因为任何与颜色的关系在历史上都是偶然的,所以有可能认为我们自己与颜色的关系是不同的,生活的颜色是不同的,因此生活的方式也是不同的。我们认为这件衣服不仅是一个例子,而且是一个不寻常的开场白,一个深入探究日常生活中奇异的、强大的、无处不在的、几乎看不见的色彩作品的机会。
与这件衣服的交锋在很大程度上是典型的:几天后,人们对这件衣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产生了网络上的“热销作品”,关于这件衣服颜色的争论就平息了。然而,这条裙子已经进入了词汇库,用来指明从颜色上看,一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特殊关系。我们现在有了礼服(我们所采用的术语)、女装,甚至是礼服。衣服的剩余部分仍然存在;但即使没有,它也提供了进入思考和生活在色彩中的重要性。当新闻报道、社交媒体交流和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提供了任何不足以质疑确定性的机会时,这一天是不会过去的。我们经常被对现实的各种不同的评估淹没,而且很明显,我们对这些评估基本上是视而不见的。仪式参与,不安全的立场,硬化的心,批评那些不同的信仰是远远超过规范。然而,色彩有能力通过自满和粉碎——可能重新安排——我们的现实。那么这里发生了什么?
2.颜色物质
这件衣服表明有必要将色彩问题提升到一个在流行语或理解日常生活文化中很少提供色彩的重要程度。这件衣服,如果天真地看,有点像文化研究451 惊讶。毕竟,为什么会有人关心它是蓝色和黑色,还是白色和金色?这件衣服摸过、拍过、弄乱了什么?它对我们自满的色彩可靠性感到震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色彩必须从阴影中被引导出来,在哲学、科学、艺术史和批评的实践中,以及讽刺的是,在艺术本身的实践和流通中,色彩既受到尊重,又受到约束,既被提升,又被贬低,在文化上被美化和隐形。
重视色彩作为分析对象有着悠久而深刻的谱系。几乎每一位哲学家都曾在某个时期研究或思考过颜色:从亚里士多德到埃利奥兹,许多浪漫主义者都写过关于颜色的文章:从达芬奇到弗朗西斯培根。许多热爱色彩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对色彩和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包括约翰·盖奇、大卫·埃尔金斯、米歇尔·帕斯托罗、大卫·巴奇勒和迈克尔·陶西格。他提出了八个流派和蒂洛彭·恩登。关于色彩的概念,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弄清楚我们在这里是如何区分我们的项目的。
首先,福尔马尼,特别是对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颜色的研究是解释什么是颜色,而不是解释它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任务很大程度上是形而上学的:这要么是一个困惑的思想实验,要么是一个准确描述的科学现实。“色彩理论”的概念暗示了将色彩作为一个可预测的现实来保护的目标,允许操纵。然而,色彩和色彩理论的哲学本身并不存在于生活之外;它们发展和循环与色彩的居住方式有着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它们在一种活生生的颜色感中发展,并进一步影响颜色是如何被理解和生活的。然而,他们与活人没有必要的联系。他们既不完全反应也不排除活生生的颜色,也不适当地关注颜色如何构成日常生活的变化。虽然文化是由理论所影响的,但它并不是从理论上生活的。通过将日常生活和生活文化作为色彩的基础,色彩可以被认为是其完全构成和偶然的作用。第二,很多关于色彩的文章都存在于科学或艺术的问题之中。一方面,在科学中,颜色被看作是基本的:作为化学、光学或欧洲现象;另一方面,在艺术中,颜色被看作是代表性的:作为艺术家、工匠和建筑师有意使用的表达材料。绘画中的色彩几乎是为正确讨论色彩的方式奠定基础的典范。即使是像大卫·巴切勒(2000)这样的画家/知识分子,在他深思熟虑的作品《发色团》中,通过各种颜色的文化表现,并断言“颜色是反学科的”(第97页),他最终还是回到了艺术批评的学科。甚至像约翰·盖奇的《色彩与文化》(1993)这样的作品,人们可能会有合理的期待452 J.D.Slack和S.Hristova前景生活在文化中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来自艺术的证据,也损害了日常生活。在不影响这类作品的辉煌的前提下,我们注意到这种回归纪律的效果影响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无法预见日常生活中色彩的构成位置。
第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哲学、科学和纪律上的色彩遭遇——主要是西方白人男性提供的——在相互争论的非常自信的情况下,告诉我们,我们真的可以自由地看到不同的颜色。似乎没有人对颜色有最后的定义。似乎没有人真正“了解”颜色。这种缺乏一致性的情况正好适合我们,因为它指出了从偶然性角度考虑色彩的可能性,以及文化上不断变化的人际关系。这种偶然性——除了认识到颜色的力量之外,它已经被表达出来了——已经被设置在侧面,让它停留在阴影中。
在文化研究中,我们对颜色的定位是不同的;人类和社会生活的东西可以理解为颜色的叠瓦,颜色的谈判和斗争。在借鉴文化研究对理解文化、差异、身份、技术和影响的贡献时,我们拒绝了理解文化和颜色的任务,而是建议我们将文化视为颜色。正如Taussig(2009年,第8页)所说,借鉴威廉·伯罗斯的观点,色彩是“一个有机的实体,与人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借鉴维克多·特纳的作品,“色彩从根本上参与了从人体中创造文化”。我们不重视文化的人文性,即人与人的整体联系。艺术、物质、生命、想象、大众、日常、关系和差异的关系,以及成为。简而言之,颜色是构成文化的所有要素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与文化分离和相关的。
我们所提出的色彩定位,要归功于文化研究、文化理论、性别研究、技术体系、动物研究、环境研究、自制哲学和影响研究中文化理解方式的巨大变化。最显著的是,在拒绝二元体(文化和技术、男性和女性、人类和机器、人类和非人类动物、自然和文化等)的主权时,也许最显著的问题已经成为关注分裂和分化的过程、杂交和联合的产生、以及异质性的表达,以及斗争、谈判和形成的过程。
我们在重新思考二元(文化和色彩)时提出的转变,最容易通过思考和超越电子人的概念来传达。如果我们重温Brie-fly Donna Haraway(1985)的《电子人宣言》,我们注意到其主要贡献在于命名(并由此指出)人类与文化研究453种动物、动物-人类和机器以及物理和非物理世界之间的共同构成关系。电子人反对男性/女性、黑人/白人、人类/动物、人类/机器、有机/技术、自然/文化等之间的二元区别。它坚持认为,生物同时是“动物和机器”,并且“以模糊的自然和做工来创造世界”(第66页)。认知科学家也有类似的说法。例如,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在其“我们一直是电子人”(Clark 2003)的主张中反对将人类作为工具使用者的概念,赞成将人类作为基本的生物技术。对于克拉克来说,人类/电子人一直都是一个“合并与联盟”(第7页)、一个“生物技术合并”(第6页)、一个“协商联盟”(第6页)和一个“文化、技术和生物学相当好地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和异质的发展矩阵”(第86页)。最终,Haraway放弃了她与电子人的争论,声称电子人已经无法维持批判性思维,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包容性的“伴生物种”概念。她当时的关键主张是,“没有一个合伙人预先存在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永远不会一劳永逸。历史的特殊性和偶然的易变性规则一直延伸到自然和文化,语调文化(Haraway2003,第12页)。她坚持认为,“现实”是一个活跃的动词(第6页),而不是一件事。
电子人的局限性在于:它被采用的方式既过于“我们”,又过于容易被当作“事物”。“伴生物种”和“自然文化”都是改进,因为它们与我们的关系不大,但它们仍然太容易被表达出来,并且仅限于“物种”或有机体。正如Haraway所观察到的那样,(她的)电子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打算从事女权主义工作;可以说,“伴生物种”是为了在21世纪初将这种关注延伸到动物身上。安迪·克拉克的电子人完全是关于人类的。因此,正如电子人、伴生物种和自然文化一样,有理由继续推进。当我们把这种思考的形象延伸到思考颜色的时候,很明显,从事物或我们与非人类动物的关系的角度来思考,并不能把我们生活中的关系带到非常远的颜色上。正如德勒兹所说,“绿色”不是一个事物,一个“存在”,而是一个“不存在于在表示事物的命题之外”的属性(德勒兹,1990年,第21页)。当我们陈述“绿树”时,我们积极地将其归因于绿色;这是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件事。正如德勒兹所说,这就是“绿色”。我们建议,事件(对绿色)将“元素”与“命题”联系起来;它是一个将矿物、液体、空气、生物体、神经过程、光、视觉、历史、哲学、社会结构、文化实践、系统色彩和语言混合在一起的事件。此外,颜色的“到绿色”意味着例如,我可以选择颜色。也就是说,我们的颜色来自颜色中的某个位置。我们绝不会对着色行为感到陌生。当我们绿化树木时,我们在颜色上这样做,从颜色的位置,进一步着色。454 J.D.Slack和S.Hristova 我们自己。根据Jussi Parikka(2015)的工作,他提出了一种“地质”方法来理解媒介,我们理解了一个简单的命题,即树木是绿色的,而它似乎将颜色仅仅作为表面或属性来表现,事实上,它表达并颁布了深层的地质、生物、材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0229],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