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动员和政治发展
卡尔·多伊奇
社会动员是一个整体变化过程的名称,这种变化发生在从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变的国家的大部分人口中。它表示一个概念,其中包括一些更具体的变革过程,如居住地、职业、社会环境、面对面的交往、机构、角色的变化和行为方式、经验和期望,最后是个人的记忆、习惯和需求的变化,这个需求包括群体归属和个人身份的新形象新模式的需要。单一的变化,甚至更多变化的累积往往影响、有时甚至会改变政治行为。
社会动员的概念不仅仅是指刚刚列出的变化的集合的这样一个简短的方式,包括该清单的任何扩展。它意味着,这些进程往往会在某些历史情况和经济发展阶段相结合;这这些情况在国家之间是可识别的和经常发生的;它们与政治有关。在本文中,每一个要点都将被采纳。
让我们重申,社会动员是发生在经历过现代化地区的众多人身上的情况,在文化、技术和经济生活中,先进的、非传统的实践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被引进和接受。因此,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它并不完全相同,但社会动员处理的是它的一个主要方面,或更好地处理其后果中的反复出现的问题。这些后果一旦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就会影响到进一步的现代化进程。因此,作为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可以在短时间跨度内处理的问题,似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作为其持续的方面之一,并作为一个重大的原因,在众所周知的反馈或循环因果关系中。
从较长时间的角度来看,这种反复关联的术语,远远高于任何偶然的预期。因此,任何形式的社会动员,如进入市场关系和货币经济(因此远离务农和易货)应将伴随着或后跟一个客观联系频率的显著升高,或在接触大众传媒的沟通,或变更住所,或在政治或准政治参与。因此,这个概念的含义是断言一个经验事实——即明显频繁的关联——这个断言可以通过经验检验。
这种社会动员的概念早在直觉上就被认为是一种历史的回忆或诗意的形象。它是基于1793年法国征兵的历史经验,以及1914 - 18年德国“总动员”的历史经验,以其在社会和情感上的影响,包括著名的恩斯特·吉格(Ernst Jiinger)在内,都戏剧性地描述了它的社会和情感影响。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一些著作中讨论的一个有关的概念就是长期和全世界的“基本民主化进程”。这些概念表明,摆脱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旧承诺,以及进入新情况的新形势,新形式的行为是相关和需要的,以及必须作出新的承诺。
因此,社会动员可以被定义为,在这个过程中,旧社会、经济和心理承诺的主要集群被侵蚀或破坏,人们就可以获得新的社会和行为模式。正如爱德华·希尔斯正确指出的那样,“动员”和曼海姆“基本民主化”的原始图像暗示了这个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1)离开旧的环境、习惯和承诺的阶段;(2)将动员人员归纳为一些相对稳定的群体成员、组织和承诺的新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士兵们从他们的家里和家庭中被动员起来,并动员到他们服役的军队中。同样,曼海姆也提出了大量人远离潜在和实际参与大众政治的形象。
使这幅图像更具体是政治理论的任务;使其成为可以通过证据证实的形式;并将其发展到一个问题'如何? '可以用“多少?”这个问题来补充。在其直观的形式中,社会动员的概念已经伴随着一些图像的增长和上升的曲线(在其直观的形式中,社会动员的概念已经带有一些越来越多的数字和上升曲线的图像)。就这样的曲线可以量化和描述社会动员的组成过程而言,学习曲线上升的速度,无论是显示任何转折点,还是跨越任何阈值,都是有趣的, 他们描绘的过程有与以前的不同的副作用。这些方面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对政治制度的执行以及各国政府的稳定和能力有任何影响。
Ⅰ分析公式
让M代表社会动员的广义(一般化)过程,让我们把它看作是代表人们可以重新投入的一般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M可以用任何一个人在15到65岁之间的平均概率来衡量,在他的一生中,或者可能会经历,从旧的生活方式到新的生活方式。
为了更准确地定义这种变化,有必要做三个假设:(1)有不同形式的与政治有关的社会再承诺与政治有关;(2)这些形式往往相互关联;(3)这些形式倾向于相互加强彼此的作用。在调查中,还有两个问题应该被注意:(4)每一种形式可能有一个阈值,其中一些阈值的影响可能对形式产生重大变化;(5)某些或所有这些阈值,虽然在数量上并不相同,但可能彼此之间有显著的联系。对于这些社会动员的构成过程,我们可能会选择符号m1、m2 m3hellip;mn来代表他们。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机械、建筑、装置、消费品、展示窗口、谣言、政府、医疗或军事实践,以及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宣传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后,m2可能代表一个更窄的概念,仅仅接触这些大众媒体。m3可以代表住宅变更;m4城市化;m5代表农业职业的改变;m6代表素养;m7代表人均收入;等等。
我们的m1可以代表以任何实质性的方式接触到现代生活重要方面的人口百分比;m2代表大众传媒体的百分比,即大众传媒的受众; m3代表已改变其居住地(或其所在地区、省或州)的居民的百分比; m4代表城镇总人口的百分比;m5代表非农职业占总收入的百分比;m6代表受教育者百分比;m7可以简单地用国民生产净值来衡量,也可以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在此阶段,在汇编的证据中,指标和定义的准确选择必须很大程度上受到统计数据的可利用性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使用联合国出版的数据和定义可能是最令人满意的,例如在联合国人口年刊、联合国世界社会调查、联合国统计年鉴和许多更专业的联合国出版物。
在现代高度发达和充分动员的国家中,m7应高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600美元;m1、m2和m6都应高于50%,即使是在满足国内消费后产生大量农业盈余的国家;甚至是m3,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居住的变化似乎也高于50%。在一个极度不发达的国家,如埃塞俄比亚,m7远低于100美元,其余的指标可能接近5%甚至更低。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国家的发展状况变得越来越不像埃塞俄比亚,而更像美国的发展情况,所有这些指标都倾向于朝着同样的方向变化,尽管它们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变化。因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所称的“指标的互换性”;如果这些指标中有一个(甚至数个)是缺失的,则可能在许多情况下被其余的指标所取代,或被其他指标所替代,而基本社会进程的一般水平和方向仍然是明确的。然而,这个特征只是作为第一个近似值。不同指标之间的滞后和差异可以揭示出学生对政治的兴趣,其中一些差异将在下面讨论。
然而,社会动员的第一个主要问题是,它确实假定了一个单一的基本过程,其中特定的指标只代表特定的方面;这些指标是相互关联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互换的;这种复杂的社会变化过程与政治的重大变化有着显著的关联。
社会动员的总体指标M是二级指标;它衡量一阶指数m1 hellip;mn之间的相关性。此外,它应该表示(n 1)的指数与它的前任相似的概率,不管n的大小有多大,只提供了索引本身的适当选择。换句话说,断言社会动员是一个“真正”的过程,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国家,也就是去断言这些情况下断言存在很大和潜在的无限数量的可能的测量及指标,所有的测量和指标相互关联并且由和现实情况的相关性的大小和强度进行测量。
当然,在实践中,可用的测量和指标的范围很可能是有限的,而且通常不需要对任何特定的时间和国家进行编译,即使所有这些数据都是可以找到的。在这个国家,人们通常的目标是经济:从最小的数据体中获取最大的有用信息。在上面列出的社会动员的7个指标,如m1到m7,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情况有相当不错的第一印象。它们的选择部分基于可用性和方便性,但也因为它们不太紧密相关,因此比起其他指标来说不完全可以互换。
所选择的七个过程中,每一个都可以由几个不同的子指标来衡量,但在每一个情况下,这些子指标都紧密相关,并且几乎完全可以互换。例如,读写能力可以用在超过15岁或以上的人口的百分比来衡量,也可以用在7岁以上;它可以被定义为识别几个单词,或连续阅读,或写作的能力。每一个特定的定义都会产生一个不同的数字答案,但只要每个国家,或者在同一个国家内的每一个时期都使用相同的定义,那么每一个标准都会揭示出同样的情况。如果适用于1920年到1950年的摩洛哥,那每一项测试都将表明,受过教育的摩洛哥人的数量开始超过识字的法国人的数量,这对其政治前途有着明显的影响。
同样地,可以以超过2000人或超过5000人、超过2万或5万居民的所有地方的人口来衡量城市化,也可以以不太令人满意的标准,即从所有有宪章的地方或政府的城市形式的人口来衡量。每一个测量标准的都揭示了在1870年到1920年间芬兰或者1900年到1940年间的印度城市大规模发展的相同过程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弗雷德里克·e·提贝茨(Frederick e . Tibbetts)最近提出的一项未发表的研究表明,加拿大城市增长的不同指标之间有着密切可互换性,就像他们对该国法语和说英语的人口的同化和分化问题一样。Tibbetts发现,在近几十年里城市化进程已经超过了法裔加拿大人的英语学习进程;他发现,在城市居民中,通常在非农业职业中,越来越多的人只会法语。这一发展的政治意义主要是集中在魁北克,从他的观察中可以明显得出,在1951年魁北克(忽略蒙特利尔)人数占加拿大总人口的21%,而其中一战二战的的退伍军人分别只占4%和7%。
在本文提出的社会动员的七大指标中,经济发展与受教育率之间的关联性较低,差异更明显。埃塞俄比亚和缅甸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50美元,埃塞俄比亚的受教育率不到5%且政治稳定;而缅甸的文字数超过了45%但政治局势动荡。在印度,喀拉拉邦是受教育率最高的邦之一,却在上世纪50年代末选举产生了一个共产主义政府。
因此,寻找两种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有用的:(1)7个主要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有多大,(2)不同的案例有多有趣?关于第一个问题,已经指出7个主要指标的数值将不相同。然而,我们认为每一个指标都是一个单独的尺度,每个国家从排名上都可能处于从前五到后五的任何位置,然后我们可以衡量一个国家排名在每个指标上的关联程度。从数据的总体印象来看,我应该推测,这些秩序相关性应该有大约0.6到0.8之间的相关系数,占观测值变化的一半。至于第二个问题,每一个案例展示实质性差异的一些主要指标必须分开研究,但刚才提到的缅甸和喀拉拉邦的例子,表明这种情况很可能还原调查,而比较的指标可能会为政治科学家提供一个粗略的但也许有用的研究手段。
为了更精确的研究,可以引入两个阈值的概念。第一个是重要性的阈值S,即,在以下的数值下,没有明显偏离传统社会的常规运作的数值,在其不变的功能中也不会产生显著的干扰。对于每个特定的指标m1 到m7,我们应该期待找到一个相应的特定的重要性的阈值,即为s7到s1;我们的社会动员的概念应该意味着,一旦几个主要指标或超过这个重要性的阈值,其余指标也应达到或超过各自的重要性水平。事实上,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应该再次表明,如果把社会动员作为一个整体过程来考虑,可能有多大程度的现实。
第二个阈值是社会动员过程中实际或明显的伴随效果发生重大改变的临界程度。在我们上面列出的每一个指标的水平上,社会或政治方面的影响出现了哪些变化?
识字的指标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如果比较上世纪五十年代许多国家的受教育率和出生率,就会发现相较于受教育率得到大幅度提升,十五岁以上的人依旧占总人口的10%到60%,二者并没有很大的关系。然而,在80%的受教育率水平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在相同的国家中,受教育率超过80%以上的国家,每年的出生率都在3%以下。为了进行进一步的测试暂时假设:受教育率超过80%可能表示一个先进的和彻底的社会动员和现代化阶段会影响那些从国家出生率中表现出来的家庭生活的亲密模式。这样的假设需要其他的证据来证实,但即使在试探性阶段,它也能说明我们的观点。如果这是真的,那么80%的受教育率将是社会动员的关键性指标。
我们把受教育率称为M6,可以把c6作为这个尺度上的临界值,然后把它设为80%。要进一步调查,看看其他关键变化是否也发生在接近80%的受教育率水平附近,这将是一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c6可能是这个指标的临界临界阈值。如果重要的副作用应该在不同的受教育水平上显示出关键的变化,我们可能必须假设几个临界值的临界值,可能会写出c6#39;, c6',等等。
其他指标在其特定尺度上可能有自己的临界阈值。 例如,大多数受教育率80%以上的国家城市化也超过了40%,在城市化规模的40%水平上,80%受教育率以上的明显的副作用也可以观察到。 如果我们所有七个指标都可以找到关键性的这种不同但相关的阈值,那么社会动员的概念可以被表达为一个概率,如果对于一些国家,不同的指标应该显示等于或大于其各自的关键水平,那么任何相关(第n 1)个指标也将被证明在等于或高于自己的临界阈值。
迄今为止所说的大部分内容可以用简洁的符号加以概括。如果我们将P作为传统的概率符号,将Ms作为社会动员整体进程的符号,就意义的阈值而言,MO作为临界关键阈值的同一过程的符号,那么我们可以简要介绍社会动员的总体概念如下:
这些速记公式都不需要在这里进一步评论。他们只是总结了前几页的更多内容。 发现这种不合格的制度的读者可能会跳过它们,因此,只要他们遵循口头论证,就不会有任何损失。
Ⅱ对发展政策的一些影响
在任何一个发生社会动员的国家,都带来了政治上相关的人口阶层的扩大。这些政治上相关的阶层是一个比精英更广泛的群体:它们包括在政治中必须被考虑的所有这些人。例如,在加纳、尼日利亚或美国,码头工人和工会成员不一定是这些国家的精英,但他们很有可能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有所作为。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政治进程通常不包括大量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农业、传统和政治冷漠的村民,但它包括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市场农民、金钱用户、打工仔以及在城镇和农村的广播听众和学者。这些人民数量的增长给政治实践和体制的改革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由于未来的增长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过去的趋势和数据中得到估计,因此,政治压力的一些预期增长——我们可以称之为潜在的政治紧张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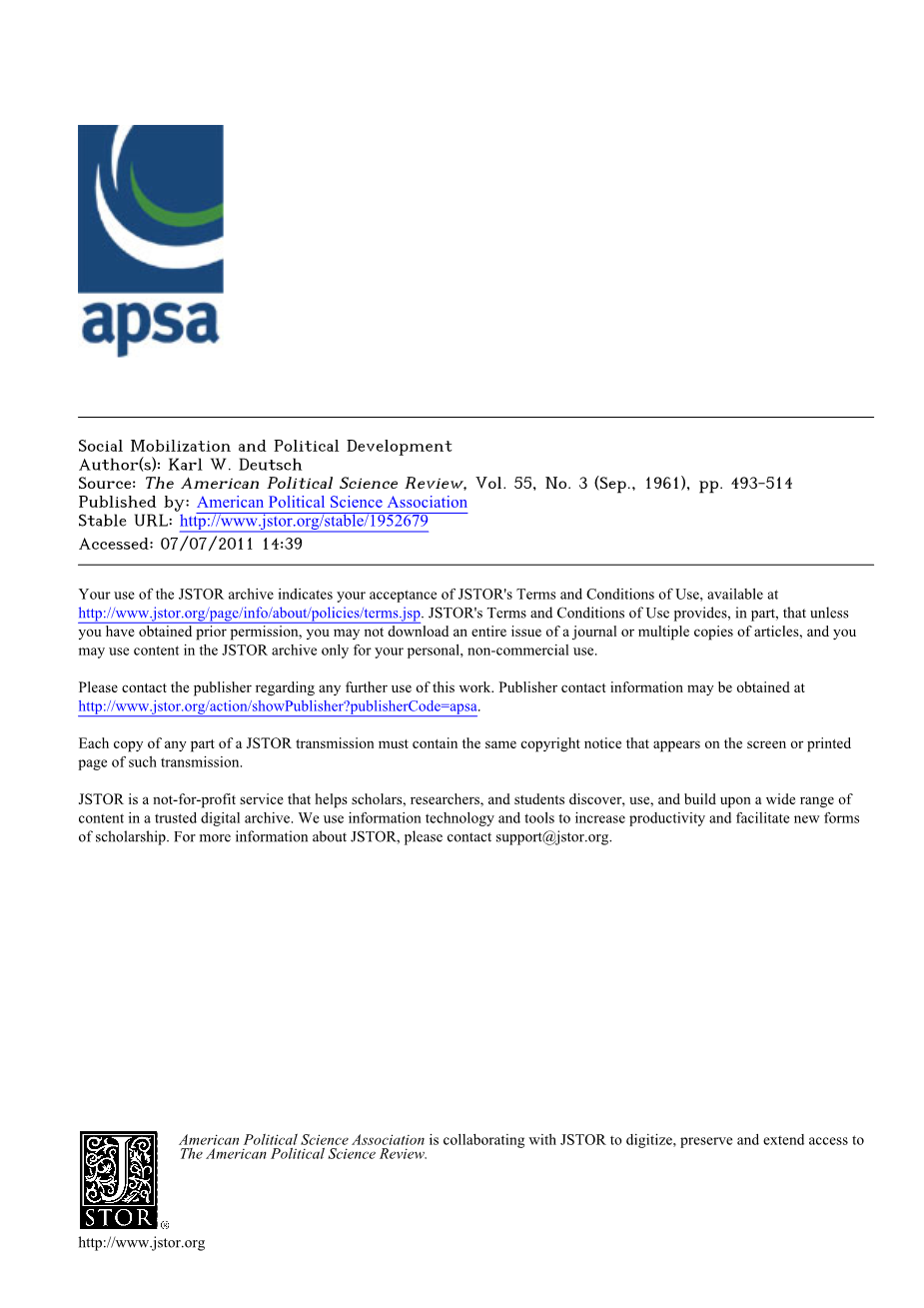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2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