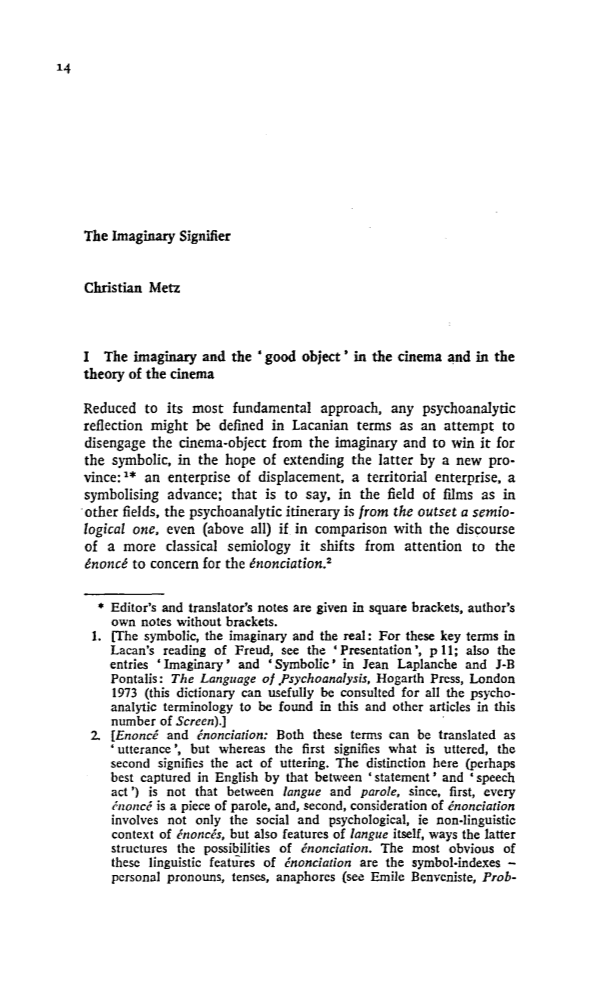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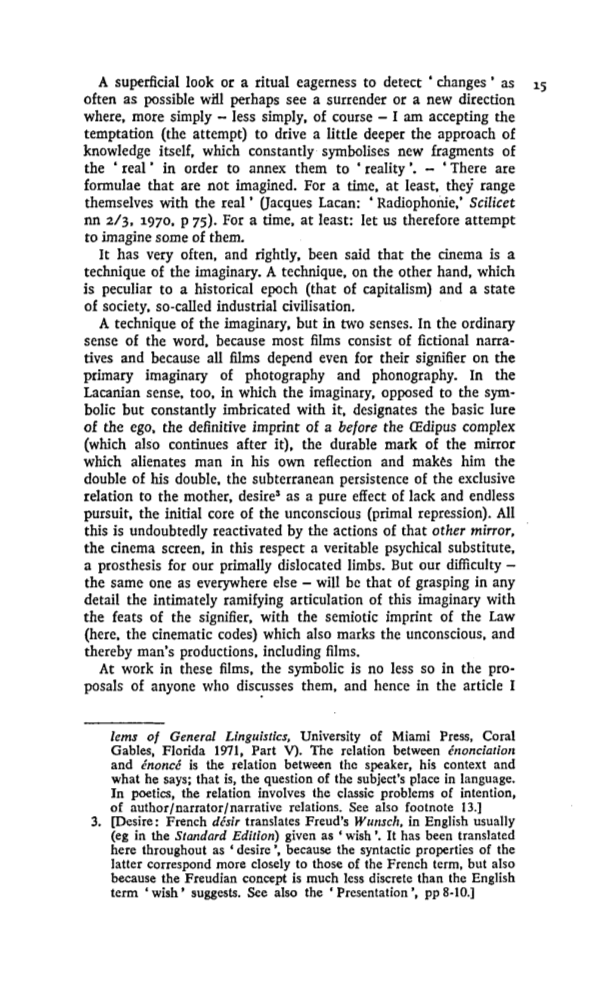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63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翻译自克里斯蒂安·麦茨《想象的能指》第一章第三节
3.认同、镜子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能够对电影能指的知识做出什么贡献”这就是我提出的梦——问题(希求符号化的科学的想象界),而且在我看来,我现在还几乎没有怎么展开它;这个用语意味着,问题仍然是:我还没有答案,我只是关心,我希望把它说成什么(直到人们把它写下来时,才会知道这一点),我只是提出我的问题:这个没有解答的性质是一个必须谨慎地对待的性质,它对任何认识论的程序都是基本的。
因为我希望标明它的区域(好像一些空盒子,其中有的不等我就开始充满了,而且,这样要好得多),工作方向不同的区域,尤其是最后一个方向的区域,我特别关心通过精神分析探讨能指,所以,我现在必须描述这最后一个盒子里的某些东西;必须进一步地而且是在无意识的方向上更清楚地掌 握促使我写作的关于调查者的分析。当然,这一开始就意味着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在使电影区别于文学、绘画等的电影能指的特殊性中间,哪些是从其本性就是最直接地求助于唯有精神分析才能提供的一类知识?
知觉、想象
电影能指是“知觉的”(视觉与听觉)。文学的能指亦如是,因为写下的链条必须被“读”,而且,它还包含一个更加受限制的知觉范畴:只是字母,书写、绘画、雕塑、建筑、摄影的能指也是如此,而且仍然受到限制,不同的是听知觉的缺席,视觉本身中的某些重要维度如时间和运动的缺席(很显然存在着看的时间,但是,被看对象不是被嵌入一个明确的时间段落从外部强加给观众的)。音乐能指也是知觉的,但是它像其他能指一样,比电影能指的 “外延”少:这里它缺的是视觉,即使是在听觉上它还缺少言语(歌唱除外)。 总之,引人注目的是,和其他表达手段相比,电影有着“更多的知觉”,如果这 种说法是可以允许的话;它调动起数目众多的知觉轴。(这就是为什么电影有时被描述为“各门艺术的综合”;这并没有很多用意,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 局限在知觉注册的数量单位上的话,那么,电影确实在其自身囊括其他艺术的能指:电影可以为我们展现画作,让我们听音乐,电影是由摄影构成的等。)
反之,如果把电影同戏剧、歌剧和其他同类的演出相比较,那么,这种数量上的“优势”好像就消失了。后者也同时包含着视觉和听觉,语言的听觉 和非语言的听觉、运动、真实的时间进程。它们在别处区别于电影:它们不是由影像构成的,它们提供给眼睛和耳朵的知觉是在真实空间(不是一种被拍摄下来的空间)被表现的,这个空间与演出期间公众所占据的空间一样; 观众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是在他们眼前由现场的人或道具制造出来的。这 里涉及的不是虚构问题,而是能指的明确性特征问题:不论戏剧表演是否摹仿一个虚构故事,只要有摹仿必要,它的“动作”就仍然是卷入真实时空的真实的人,在像观众席一样的舞台或“场地”安排的。“其他场地”,因而也就不那样称呼了,是电影的银幕(从一开始就更接近于梦幻):在那里展现的依旧多多少少是虚构的,而展现本身也是虚幻的:演员、布景、人们听到的言词全都是不在的,都是被记录下来的(好像是一种记忆的痕迹,它直接就是如此, 在此以前并没有成为某些别的东西),如果被记录的不是一个“故事”,不是为了纯粹虚构的幻象,那么,这仍然是真实的。因为,它就是能指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它是被记录下来的,是缺席:“包含”巨大的布景、事先安排好的战斗、涅瓦河上的冰的融化以及整个生命时间的一小卷带孔的胶片带,它还可以被封存在熟悉的尺寸上有限制的圆铁盒子中,这是它并不“真的”包含诸如此类东西的明证。
在戏剧方面,莎拉bull;贝恩哈特可以告诉我,她是菲德尔,或者,如果表演是在其他时代并且拒绝比喻表述的话,她可能会像在某些现代类型的戏剧中那样,说她是莎拉bull;贝恩哈特。无论如何,我看到的应当是莎拉bull;贝恩哈特。电影方面,她也可以说出同样的两种话,但是,正是她的影子把它们呈现给我(或者说,她在她自己的缺席中呈现它们)每一部影片都是虚构片。
成问题的不只是演员。现在有了没有演员的戏剧和电影,或者说,在这里,演员至少已经不再承担在传统演出场面中刻画人物性格的全部功能了。 而莎拉bull;贝恩哈特的真实只是作为一个物体、道具的真实,例如一把椅子。 在戏剧舞台上,这把椅子,比如在契诃夫那里,可以装扮成忧郁的俄国贵族每晚都要坐的那把椅子;反之(在尤奈斯库中),它还可以向我表明,它是一把戏剧的椅子。但是,它毕竟是一把椅子。在电影中,它将不得不类似地在两种姿态(和许多其他间接的或更巧妙的姿态)中进行选择,但是,当观众看着它时,当他们必须认可选择时,它是缺席的;它交给观众的是自己的影子。
电影的特性,并不在于它可能再现想象界,而是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是想象界,把它作为一个能指来构成的想象界(这两者并非不相关,它之所以能再现它,因为它就是它;不管怎样,即使它不再现在它,它也是它)。创造虚构的意图的重复(可能的),以总是已经完成了的、创造了能指的第一次重复为先导。按定义,想象界在它自身之内把一定的在场和一定的缺席结合起来。在电影中,它不只是虚构的所指(如果有的话),它成了以缺席方式的出席,它从一开始就是能指。
这样按其感知注册项目以及与其他艺术相比有“更多知觉”的电影,一旦面对这些知觉的重要地位,而不是它们的数量或多样性时,就比其他艺术有“更少的知觉”了;因为,它的知觉全都是虚构的。更正确地说,这里的知觉活动是真实的,但是,感知到的却不是真实的物体,而是物体的影子、幻 影、替身和一种新的镜子中的复制品。可以说,文学归根结底只是由复制品构成的(写下的语词描述着缺席的事物)。但它至少不是以在银幕上呈现的 (给的和拿的同样多)、全都是真正看到的细节的方式把它们呈现给我们。 电影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在于其能指的这种双重特点:不平常的知觉资源,但同时还带有某种异常深刻的非现实性印记。电影比其他艺术更多地或以更独一无二的方式使我们卷入想象界:而且,为了使它立即全部地转变成它自己的缺席,而鼓动起全部的知觉,这不过是最理想的能指的出场。
感知一切的主体
因此,电影像镜子一样。但它在一个根本点上不同于原初的镜子:尽管如在镜中,一切都可以得到反映了,但有一件事,并且只有一件事,不能在其中反映:观众自己的身体。在某一个掩体上,这面镜子突然成了透亮的玻璃。
在镜子里,孩子觉察到家里熟悉的物品,尤其是其中还有他把他抱在怀里面对镜子的母亲。但是,他首先觉察他自己的映像。正是在这里,一次认同(自我的形成)获得了它的某些主要特征:孩子看到自己作为一个他者,而且是在一个他者的旁边。这另一个他者向他担保,前者是在象征界的注册中真正第一次出现的东西:通过她的权威,她的认可,接着是她的镜像和孩子的镜像的相似(两者都有人形)。这样,孩子的自我通过对与其类似的人的认同而形成,而且,这是在同时是隐喻和换喻两种意义上形成的:镜子中的另一个人,只是身体自己的反映,而不是他的身体,他是他的相似。孩子认同自己作为对象。
在电影中,对象仍然保留着:虚构的或非虚枸的,银幕上总是有某些东西。但自己的身体的映像却消失了。电影观众不是孩子,同时,真正处在镜像阶段(从大约六个月到十八个月)的孩子还肯定不会“懂得”最简单的影片。因此,使得观众在银幕上缺席成为可能的——更正确地说,尽管他缺席,但影片仍能明白易懂地进行下去——因为观众已经懂得了镜子(真正的镜子)的经验,因而不必在其中首先认出自己就能构成一个物象的世界。就此而言,电影已经处在象征界一边(这只是预期的):观众知道,物象存在着,他自己作为一个主体存在着,他对于他者而言成为一个对象:他了解自己,了解和他同样的人。把这种类似在银幕上向他描述已不必要,原来他在孩子时代的镜子里就已经了解到这一点了。正如所有其他广义的“二次”活动一样,电影实践预先就假定,自我和非我的原始无差别状态已经被克服了。
那么,观众在电影放映期间究竟认同什么呢?因为他肯定必须与自己认同:按原初形式下的认同现在对他已经不再是必须,而他在电影中要继续依赖那种没有它就没有社会生活的永久的认同游戏,否则,影片就会变得不可理解,比最不可理解的影片还要不可理解得多(这样,最简单的交谈都预先假设了我和你的交替,因此预先假设了两个对话者互相认同的态度)。在 他者之间的一种社会实践的特殊情况下,即在电影放映的情况下,拉康甚至以最抽象的论证方式来论证其根本作用的这种连续的认同采取什么形式?这种认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构成了“社会的” (=同性力比多的升华,自身就是对弑父后同一代成员的敌对性竞争的反应性)。
显然,观众有机会认同虚构的人物。但是,还必须有虚构的人物。因此这一点只对叙事性一再现性的影片有意义,而与电影能指本身的精神分析结构无关。在程度不同的“非虚构”的影片中,观众还能够同演员认同,在这种影片中,后者呈现为演员而不是人物,因此,还被呈现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可见的人),因此还可以产生认同。但是,这个因素(即使加上前一个因素,从而覆盖大量影片)也并不充分。它只是以自身的若干形式标明了二次认同(在电影过程本身的二次认同,因为在任何其他意义上,除了镜像认同以外,所有的认同都被视为二次认同)。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7638],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