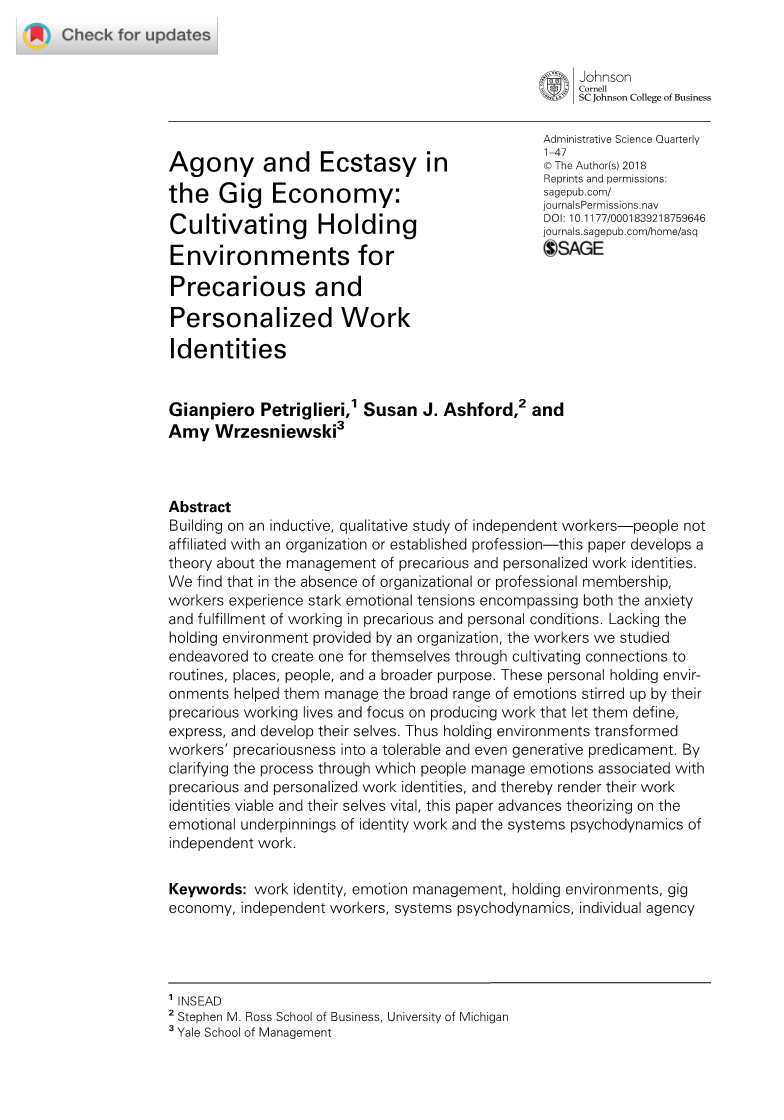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47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零工经济下的痛苦与狂喜:
为不稳定的、个性化的工作身份创造稳定的环境
Gianpiero Petriglieri, Susan J. Ashford, and Amy Wrzesniewski
摘要:本文在对自由职业者(不隶属于组织或既定职业的人)进行归纳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关于不稳定和个性化工作身份管理的理论。我们发现,在缺乏组织或专业成员的情况下,员工会经历严重的情感紧张,包括在不稳定和个人条件下工作的焦虑和成就感。由于缺乏组织提供的固定环境,我们研究的自由职业者们试图通过培养与日常生活、地点、人和更广泛的目标的联系来为自己创造一个固定环境。这些个人、环境帮助他们管理由不稳定的工作生活引发的情绪,并帮助他们更加专注于定义、表达和发展所从事的工作。因此,把握环境将自由职业者的不稳定性转变为一种可容忍的、甚至是可生成性的状态。通过阐述人们管理与不稳定的、个性化的工作身份相关的情感的过程,从而使他们的工作身份具有可行性和自我的重要性,本文提出了关于身份工作的情感基础和独立工作的系统心理动力学理论。
关键词:工作认同;情绪管理;持有环境;零工经济;独立工作者;系统心理动力学;个体代理
工作身份是含义是什么?究竟需要什么才能保持工作身份? 组织学者对这些问题产生着浓厚的兴趣。关于身份工作的研究——人们为获得、坚持、修复或放弃身份所做的努力(Snow和Anderson,1987;Sveningsson和Alvesson(2003)——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迅速发展起来。学者们研究了组织背景下的身份工作,其特点是文化强、社区紧密、表达规则严格(Ibarra,1999;普拉特,洛克曼,考夫曼,2006;Reid, 2015),并展示了员工如何在不丧失个性的前提下努力适应苛刻的角色(Brewer, 1991;Kreiner, Hollensbe, and Sheep, 2006)。然而,经济波动和技术变革导致更多的人在这种强大的环境之外进行工作,比如在快速增长的“零工经济”中((McKinsey amp; Co.,2016)出现有大量的与组织松散联系的自由工作者或直接面向市场进行销售的工作者 (Ashford, George, and Blatt, 2007)。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组织和组织内的角色视为定义自己的主要参照者和主人,学者们注意到,当一个人对组织缺乏强烈的依恋时,获得并维持稳定的工作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安全感、自尊和合法性是有问题的(桑尼特1998;Alvesson and Willmott, 2002)。对于在组织和既定职业之外工作的独立工作者来说,塑造工作身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缺乏系统化角色的参照。独立工作带来的挑战与身份工作通常研究的背景不同。这是一个工作的世界,“workplace”不再是办公楼或工厂楼层的同义词(Barley,2016)。独立工作者缺乏被认为在工作中构建稳定身份所必需的安全从属关系和可预测的未来(Sennett,1998;Ashforth,Harrison,and Corley,2008)。对于这些工作者来说,能否找到制度化的框架来定位他们的身份工作,充其量也是个未知数。他们的身份没有被认可的包容边界(Van Maanen和Schein,1979),也缺乏集体认可(Bartel和Dutton,2001;德鲁和阿什福德,2010)。这些独立工作者在相较弱的环境中工作(Mischel,1973),对适当的行为没有明确的期望。Weick(1996: 44)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行动指南可能在其他地方。问题是,如果没有其他人设计的工作((Hackman and Oldham,1980年),没有给予指导的领导者(Barnard1938年;Smircich和Morgan,1982;Podolny, Khurana, and Hill-Popper, 2005),以及组织社团(Wrzesniewski, Dutton, and Debebe, 2003)这类帮助员工理解自己,理解身份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普拉特和阿什福思,2003)的组织,独立工作者的行动指南应该在哪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对独立工作者进行了定性研究,这些人长期以来都面临着社会和经济认可的不确定性,工作身份的稳定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
1 自我、身份和独立的工作
1.1 自我和身份
自我、身份及其关系的概念化和学者群体的数量一样多(Baumeister,1998;Ashforth, Harrison,and Corley,2008;Alvesson,2010;Swann和Bosson,2010; Brown,2015;Ashforth and Schinoff,2016)。我们都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自我”可能是“每个人都使用但没有人定义的词”(Baumeister, 1998: 681),而“自我”渴望被定义(Hogg,2007)。我们将身份定义为:通过个人属性(Ashforth and Mael, 1989)、关系(Sluss and Ashforth, 2007)和群体成员关系(Tajfel and Turner, 1986)与自我相关的意义(Gecas, 1982)。我们关注的是身份给自我带来的机遇和约束。身份赋予自我认知、情感、行为和社会界限,自由职业者们把自己定义为“X”(例如,内向的人,兄弟,律师)。它们描述了“X”是什么意思和它不是什么意思,证明了X是一种什么感觉,并规定了X做什么,和谁做。因此,身份使人们的内心世界和社会世界易于理解和管理(Swann和Bosson,2010)。
人们为了满足减少不确定性的基本需求而适当、协商或默认自己的身份(Hogg和Terry, 2000)、归属感(Baumeister和Leary, 1995)和自治权(Deci和Ryan, 1985)。因为一些事件将这些身份投射到负面情绪中(Petriglieri, 2015),或者追求流动、狂喜和幸福的状态,需要超越自我的边界(Baumeister,1998)。这种动态性意味着,身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平衡,产生于对一个或多个参照物的吸引和排斥”(Ashforth和Schinoff,2016: 120)。从这个角度看,身份是一种解释或表达想要或不想和某人在一起的欲望。而“自我”常常陷入两者都想要的两难境地(Bion,1961;布鲁尔,1991)。
当自我从有价值的身份中脱离时,人们会经历社会或存在的焦虑——这种情绪与预示未来的伤害有关(Ohman,2000)。社会焦虑与自我社会地位的潜在危害有关,如排斥(Baumeister and Tice,1990)或地位焦虑(Gill,2015),而存在主义焦虑又与自我的连贯性、连续性的潜在危害有关(Tillich,1952),如自由(Fromm,1942)或死亡焦虑(Becker, 1973)。身份所带来的自尊、关系和世界观保护人们免受这些焦虑的影响(Baumeister,1998),无论这种保护可多么虚幻(Knights and Willmott,1999)。
学者们越来越感兴趣的是人们如何确保自我定义,以满足需求并避免上文所提及的焦虑。随着曾经为身份提供强有力束缚的机构变得更加不稳定(Bauman,2000),身份的塑造和维护也随之出现问题(Bartel and Dutton,2001;Alvesson and Willmott,2002;) 人们努力去塑造、稳定和修正他们的身份,这被术语“身份工作”所捕获(Snow and Anderson, 1987;Sveningsson和Alvesson(2003),并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Brown, 2015)。开创性的研究集中在人们努力适应集体期望的过程中,比如研究咨询公司合伙人的行为举止(Ibarra,1999;Reid,2015),专科医生(Pratt,Rockmann,and Kaufmann,2006),或伞兵(Thornborrow and Brown,2009)这类在保持独特性的同时,在一个机构内获得舒适和合法性的职业(Kreiner,Hollensbe,and Sheep,2006)。而专注于个人参与(Kahn,1990)、成长(Sonenshein et al.,2013)和真实性(Cable,Gino,and Staats,2013)的研究也考察了这些现象与组织的关系,如永久性(Pratt, 2000)或临时性(Anteby and Wrzesniewski, 2014; Petriglieri,and Wood,2017)并从这些关系出发努力人们定义工作中的自我。
使用社会认同理论视角的学者们强调人们通过对组织的认同来追求自尊和避免社交焦虑这一观点(Ashforth, Harrison, and Corley,2008)。那些使用批判视角的学者则关注的是组织如何利用成员的存在焦虑来强加承诺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身份(Alvesson和Willmott,2002)。也有学者描述了组织如何授予社会身份,但限制个人身份的表达这一现象(Ashforth,Harrison,and Corley,2008)。其他学者将组织描述为提供世界观(Greil and Rudy,1984)和心理安全(Edmondson,1999),帮助人们在工作中表达自我(Kahn,1990)并塑造理想的身份的地方(Pratt,2000;Thornborrow and Brown,2009)。简而言之,在现有的大多数研究中,组织以及组织内部的角色和关系为身份工作提供了参照。
同样,组织往往被视为人们工作情感体验的来源和容器。学者们把情感部分看作是经验的副产品(Pizer和Hartel, 2005),它由工作环境激发并通过组织提供的视角来进一步解释情感。在这些观点中,组织煽动或抑制员工的情绪并塑造他们的表达(Rafaeli和Sutton,1989)。Gill (2015)认为,由于大多数组织的规范抑制了不加防范的情绪表达(Martin,Knopoff and Beckman,1998),学者们有了更多的途径,并更加强调认知和行为认同的工作。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独立工作中产生的情感缺乏一种束缚和翻译机制,从而使人们能够以学者们尚未充分探索的方式体验、解释和使用情感(Martin,Knopoff,and Beckman,1998; Kunda and Van Maanen1999)。
学者们普遍关注的是人们如何定位和表达自己在组织中的位置以及与组织的关系,以追求积极的影响(Ashforth,Harrison,and Corley, 2008)和防止焦虑(Jaques,1955)。这类研究关注点导致了对“演员审问而不是保护或美化自我”这一研究的呼吁((Ybema et al.,2009:314)。这些人无法或选择不加倍努力在一个组织内确保某种形式的稳定,以补偿作为工作和身份提供者的组织的不稳定,即我们所研究的主体——独立工作者(Ibarra and Obodaru,2016)。
1.2自由职业
全球化、技术变革和经济不确定性引发了“工作场所关系的深刻重组”(Padavic, 2005:113)影响了人们对职业的期望(Arthur and Rousseau,1996)和劳动力市场结构(Sweet and Meiksins, 2013)的变化。劳动力中越来越多的部分由松散地隶属于组织或直接向市场销售的人员组成。超过五分之一的美国工人在传统就业之外工作,在被认为是长期组织内的全职职位之外工作,这一比例在其他国家更高(Cappelli and Keller,2013; McKinsey amp; Co.,2016)。最近的调查表明,“最近的调查显示,“从2005年到2015年,美国经济的净就业增长在似乎出现了其他工作安排 (Katz and Krueger,2016: 7)。这些变化表明,研究一个“新世界的工作”(Beck,2000),独立工作者们承担着很高的风险负担(Beck,1992),在个人意义上也有着很多的选择(Cote and Levine,2002)。
社会学家、组织学者和心理学家都指出,研究集中在新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经济学上而忽视了人们在这些市场中的经历。在Barleyand Kunda (2001:82)指出组织理论固守与层级组织中工作相关的“僵化的工作形象”十年后,Bechky(2011)哀叹学者们缺乏对工作的意义和实践的关注。Ashford, George,and Blatt(2007)和Weiss and Rupp(2011)也对我们缺乏对当今独立工作者生活经验的理解表示遗憾。随着企业作为可靠工作提供者的地位下降(Davis,2016)和零工经济的兴起((McKinsey amp; Co.,2016),了解当代员工的经历变得越来越重要。Kalleberg(2009)认为,这些变化影响着经济、社会、家庭和人们的生活,研究它们对于建立关于当代工作的组织和经验有意义的学术研究是必不可少的(Davis,2015; Barley,2016))。
学术界已经有学者在开始做的这类研究,如硅谷承包商的民族志(Kunda,Barley,and Evans,2002; Barley and Kunda,2004),临时文员 (Henson,1996),纽约市硅谷创业公司(Neff,2012),及所有额自由职业者和创造性工作者等(Ekman, 2014),这些现有研究调查仍然在组织中工作的员工。这些研究关注员工难以补救的安全性和合法性损失,关注正处于动荡的初创公司采用标准化工作所带来的风险(Pink,2001)。学者们大多对这些现象持怀疑态度,认为自由工作的好只会存在于那些工作经历丰富且幸运的人身上,而对大多数人来说会经历一段长期的不确定,这种不确定会导致焦虑、过度工作和对稳定就业的失望情绪((Henson,1996;Jurik,1998;Smit
全文共45742字,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194]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 薪酬满意度作为工作满意度的先行因素:建立一个回归模型,确定公共和私人组织中薪酬满意度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线性关系外文翻译资料
- 胜任力与胜任力、胜任力模型与胜任力模型的比较研究外文翻译资料
- 如何提高企业网络招聘的有效性外文翻译资料
- 为初级职位招聘大学生,在制定战略和战术校园招聘计划时,需要考虑哪些问题?外文翻译资料
- 基于能力的招聘:招聘和留住成功员工的关键外文翻译资料
- 员工培训对体育门票销售人员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外文翻译资料
- 由雇主参与的创新型员工激励模式外文翻译资料
- 浅析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 ——以苏州金色未来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外文翻译资料
- 互联网背景下基于平衡计分卡的计算机绩效评价系统外文翻译资料
- 提高斯洛伐克公共行政部门招聘过程的效率外文翻译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