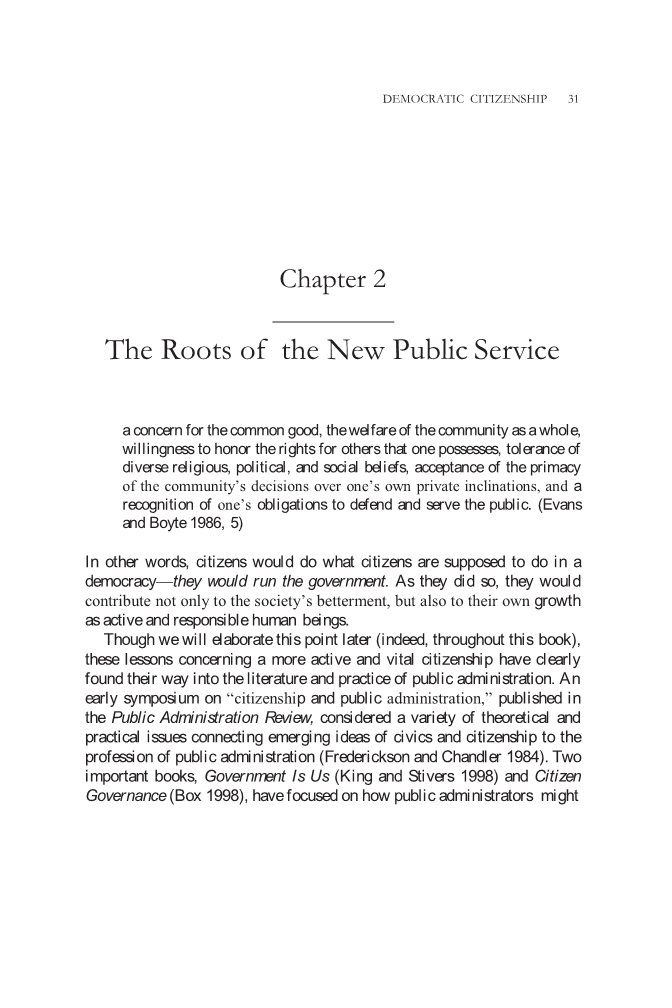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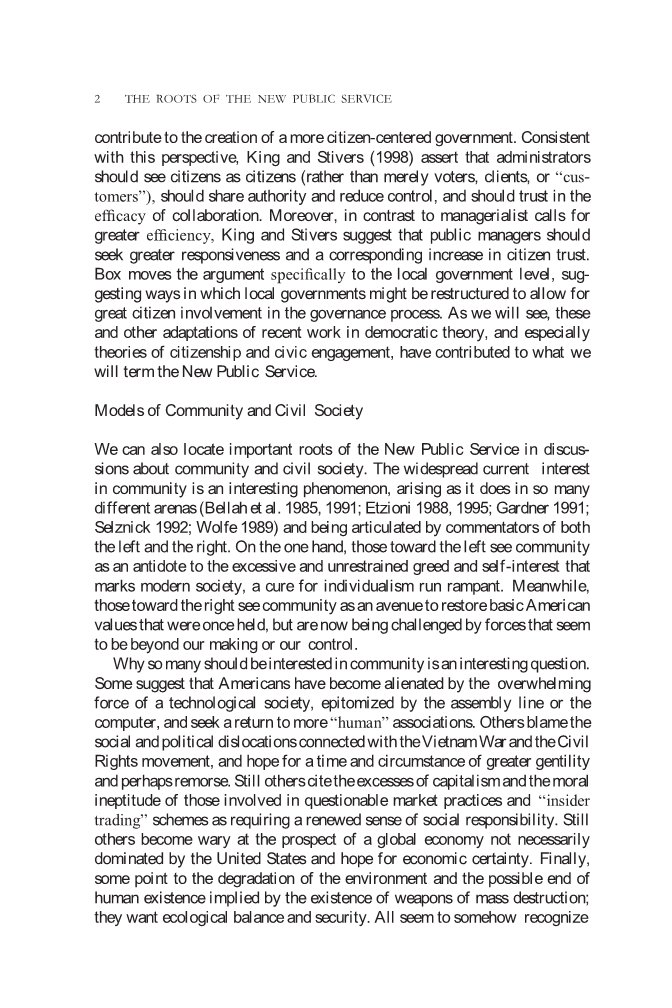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12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第二章 新公共服务的起源
关心共同利益,社区整体的福利,一个人拥有的尊重他人权利的意愿,对不同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和社会信仰的容忍,承认社区的决策重于一个人的私人偏好,以及承认一个人有责任保护公众和为公众服务。(Evans and Boyte1986,5)
换言之,公民会做一个民主政体中公民应该做的事情——他们会去管理政府。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不仅会促进社会的进步,还会促进自己作为积极负责的人健康成长。
尽管我们将会在后面(实际上是在全书中)阐明这一点,但这些关于一种更为积极且重要公民权的训诫已经很明显地进入到公共行政的文献和实践中。早期在《公共行政评论》发表的关于“公民身份和公共行政”的专题论坛就考察了各种把正在出现的公民权和公民权理念与公共行政这个职业联系起来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Frederickson and Chandler 1984)。最近,《政府属于我们》(King and Stivers 1998)和《公民治理》(Box 1989)这两本书集中探讨了公共行政官员怎样才可能会促进创立一种更加以公民为中心的政府。与这种观点相一致,金和斯蒂佛斯(1998)断言,行政官员应把公民视为公民(而不是把公民视为投票人、当事人或“顾客”),应该分享权威和减少控制,并且应该相信合作的功效。此外,与管理主义者对更高效率的要求相对照,金和斯蒂佛斯认为公共管理者应寻求更大的响应能力并相应增加公民的信任。Box将这种论点转移到地方政府层面,这表明地方政府可能会进行重组,以便让公民参与治理过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最近民主理论工作的这些和其他改编,特别是公民身份和公民参与理论,都促成了我们所谓的新公共服务。
社区与公民社会的模型
我们也可以把最近关于社区和公民社会的讨论视为新公共服务的重要来源。目前,人们对社区的广泛兴趣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种兴趣的产生在许多不同的活动场所都有所表现(Bellah et al. 1985,1999;Etzioni 1988,1995;Gardner1991;Selznick 1992;Wolfe 1989),而且并由两派的评论员联系起来。一方面,左派人士将社区视为解决过度和无拘无束的贪婪和自身利益的解毒剂,这标志着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治疗方法猖獗。与此同时,右派人士则认为社区是恢复曾经拥有的基本美国价值观的途径,但现在却受到似乎超出我们制定或控制的力量的挑战。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对社区感兴趣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有些人认为,美国人已经被技术社会的强大力量所异化了,已经成为生产线或计算机的缩影,因此他们试图向更具“人性的”社区回归。另一些人则谴责与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相联系的社会混乱和政治无序,而且他们期待着更加文雅并且更富有同情心的时代和环境的到来。还有一些人引用资本主义的过度行为以及那些参与可疑市场行为和“内幕交易”计划的人的道德无能,因此他们要求重新承担社会责任感。还有一些人对全球经济未必一定由美国主导并希望获得经济确定性的前景变得谨慎。最后,有人指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存在意味着环境的退化和人类生存的可能终结;他们想要生态平衡和安全。似乎所有人都认识到了生活已经“失去控制”,人们需要一种途径来挽回他们的生活。
总之,社区已经成为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个主题。尽管不同的作者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社区的不同方面,但是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的著作在明晰性和说服力方面堪称典范,加德纳(1991)主张,由于社区意识可能衍生于从邻里街区到工作团体等许多不同层次的人类群体,所以它可以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提供种有益的中介结构。加德纳写道:“在我们的体系中,所谓lsquo;共同利益rsquo;首先就是要保护这样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人——在法律许可范围内——都能够有自己对这种共同利益的视野,而且他们同时还能够实现种种使一个社会系统既具有价值有具有可操作性的彼此适应。冲突的利益在于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框架中的作用就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剧本”(1991,15)。尽管一个社区的共同价值观在加德纳看来很重要,但是他极力主张我们还要认识到整体性必须体现多样性。加德纳写道:
要防止整体性掩盖多样性,就必须有一种多元化的哲学,有一种容许异议的开放氛围并且有一种允许子社区在更大的团体目标背景下保持其地位和份额的机会。要防止多样性破坏整体性,就必须有一些减少两极分化、教育各种团体相互了解、建立联盟、消除争端、协商和调解的制度安排。当然,一个健康社区的存在本身就是消除冲突的一种工具。(Gardner 1991,16)
在加德纳和其他人看来,除了这些特征之外,社区建立的基础是关怀、信任和协作,它是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有效沟通和冲突解决系统结合在一起的。社区的互动本性在个人与集体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并且使得个人与集体保持一致。著名的管理理论家罗莎贝思·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or)在其早期关于社区的某些著作中讨论了这种思想。她写道:“对社区的寻求也就是对个人生活之集体中和目标的追求。将自我投人到一个社区之中、认同一个社区的权威,以及愿意支持该社区的生活,所有这一切都能够提供身份、个人意志以及按照该成员感到表达了他自己内在特质的标准和指导原则的成长机会。”(Kantorn 1972,173)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努力依赖于建立一套积极的“调解机构”,这套调解机构既可以关注公民的愿望和利益,又会提供一些将会使那些公民更好地为在更大政治体系中行动做好准备的经验。正如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2000)所论证的那样,美国的民主传统依赖于存在着民主参与的公民,这些民主参与的公民在各种群体、社团和政府单位中都很活跃。家庭、工作小组、教会、公民社团、街区群体、志愿性组织俱乐部以及社会团体——乃至运动队——都有助于建立个人与更大社会之间的联系。从集体意义上说,这些小团体构成了一种人们需要在社区关怀的环境中实现其个人利益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一种公民能够相互进行一种个人对话和评价的地方,这种个人对话和评价不仅是社区建设的本质而且也是民主的本质。
最近有许多关于公民权和公民社会概念的评论都着重探讨了美国公民明显越来越少参与政治和政府活动的原因。人民对政府的幻想似乎破灭了,他们正在从政治过程中撤出,而且在自己的私人空间中正在变得越来越孤立。例如,民意测验已经表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明显地有所下降,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度更是如此。几十年来,密歇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一直都在搜集美国人对下列问题的回答:“你相信华盛顿政府有多少时间在做正确的事情?”40年前,有3/4以上的美国人说他们“几乎总是”或者“在大部分时间”都信任政府。而今天,做出这种回答的美国人还不到1/4。对政府的信任度似乎空前的低。
然而,有人提出了种更为均衡的观点。例如,凯特林(Kettering)基金会的戴维·马休斯(David Mathews)就认为,尽管公民对政治过程的兴趣最近几年可能有所减弱,但是这种兴趣实际上并没有消失。马休斯引证了一个由凯特林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该研究项目不仅在公民中间发现了强烈的无能为力和排斥的感觉,而且也发现了深切的关怀和未发掘的公民责任意识。公民具有一种强烈的挫折感和愤怒感,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被一个由强势说客、政治家、竞选管理者以及媒体精英组成的职业政治阶层挤出了政治系统。他们认为,在这个政治系统中,选票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金钱居于支配地位。他们认为,这个系统的大门对普通公民是关闭的”(Mathews 1994,12-15)。结果,公民产生了被疏远和被孤立的感觉。
另一方面,公民仍然想要发挥作用。他们以自己的社区和国家为荣,而且他们想要有助于造成积极的变化。实际上,许多公民都不是在把自己的时间花在选举或政党政治上,而是在参与种新型的政治活动,尽管他们认为政治系统是封闭的并且难以进入,但是他们却在街坊邻里、工作团体和社团内从事一些以公民为基础的“草根”(grass-roots)活动。这些活动构成了公民权的试验场,在这里,人们正在力图建立彼此之间的新关系和更大范围的政治秩序,通过这些关系,人们不仅可以认识到现代世界对参与政治所施加的种种困境,而且还可以了解由现代环境所提供的新的活动和参与的可能性(Boyte and Kari 1996;Lappe and DuBois 1994)。
政府对于促进社区建设和公民社会似乎也有重要的作用。有趣的是,许多进步的和有远见的公民政治领袖逐渐认识到了这种活动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而且他们自己也在参与这种活动。政治领袖们正在以多种方式接触公民,他们不仅利用常规的手段而且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此相类似,公共管理者也正在就公民对政府过程的参与而重新界定自己的角色(Thomas 1995)。而且,还如同金和斯蒂弗斯(1998)所指出的那样,政府在建立、促进和支持公民与其社区之间的关系过程中能够发挥一种关键性作用。
公共行政官员是如何受社区和公民社会的影响的?他们又是怎样影响社区和公民社会的?虽然我们在本书剩余的部分中将会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可以做几点一般性的评论。首先,在存在着强大的公民互动网络和公民之间存在着高度社会信任和内聚力的地方,政府可以依靠现存的社会资本建立更为强大的网络,开辟新的对话和讨论渠道,并进一步就民主治理问题进行公民教育(Woolum 2000)。其次,公共行政官员能够为社区和社会资本的建设做出贡献。目前,有些人认为,公共行政官员的首要角色就是要建设社区(Nalbandian 1999)。另一些人则必定会认为,公共行政官员能够通过鼓励公民参与公共决策而对增进社会资本发挥积极的作用。约瑟夫·格雷和琳达·蔡平(Joseph Gray and Linda Chapin)根据其对公民参与进行广泛研究的经验评论说:“尽管公民并非总是能够获得他们所想要的东西,但是使他们参与其中则可以具体体现我们所做的工作——即把公共行政与公众联联系起来,而且这种联系无论是对于公民还是对于行政官员都会达成理解”(1998,192).这样种理解既丰富了政府,又丰富了社区。
组织人本主义与新公共行政
新公共服务的第三个重要理论来源是组织人本主义。在过去的25年中,公共行政理论家们已经与其他学科的同事们都认为,对社会组织的传统层级制研究方法限制了他们对人类行为的认识视野,而且他们都批评官僚制并且都在为管理和组织的研究寻求可替代的备选方法。从集体意义上来看,这些方法都试图把公共组织改变成为更少地受权威和控制的支配并且更加关注内部选民和外部选民的需要和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正如像马歇尔·迪莫克、罗伯特·达尔和德怀特·沃尔多这样一些学者对公共行政理论的这种流行观点所提出的对比一样,诸如克里斯·阿吉利斯(Chris Argyris)和罗伯特·戈伦比威斯基(Robert Golembiewski)这样一些学者也对20世纪后期流行的组织管理观点提出了对比。在早期的《个性与组织》一书中就探讨了传统的管理方法对复杂组织内部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阿吉利斯特别提到,关于人类个性的研究表明,从幼年期成长到成年期的人们都要经历从被动到主动、从依赖到独立、从有限范围到更大范围的行为、从表层到更深层的兴趣、从较短期的眼光到更长远的眼光、从从属的地位到平等的或优越的地位以及从缺乏了解到更多的认识这样的一种发展过程(1957,50)。相比之下,那时阿吉利斯眼中的标准管理方法(而且有人可能会认为那些标准的管理方法即便是在今天也都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似乎不是促进了雇员的发展而是抑制了雇员的发展。例如,在多数组织中,人们对自己的工作很少有控制权,在许多情况下,就其所能够做的事情而言,他们被要求服从、依附并且自主性很有限。阿吉利斯认为,这样一种安排最终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因为它限制了雇员能够为组织所做的贡献。为了在改进组织的绩效同时促进个人的发展,阿吉利斯找到了一种“管理者在有效断、帮助个人成长和培养创造力(以及)对付具有依赖取向的hellip;hellip;雇员时将会开发和运用自我意识技巧的管理方法”(Argvris 1962,213)。随着阿吉利斯研究工作的进展,他越来越集中关注组织通过被称之为“组织发展”的计划变革项目以便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途径。
我们应该注意,阿吉利斯的思想与流行的理性行政模式直接形成了对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流行的理性行政模式是由赫伯特·西蒙明确表达的。实际上,阿吉利斯在1973年就在《公共行政评论》上利用相当的篇幅探讨了这种理性模式的一些局限性(Argyris1973)。阿吉利斯一开始就指出,西蒙的理性模型与传统的行政理论很相似,传统的行政理论认为,管理部门不仅要对雇员进行培训和奖惩,而且还要规定组织的目标和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种权威是自上而下流动的正式金字塔形结构框架中进行的。西蒙对这个模式所做的补充就是集中强调了理性行为,也就是说,他集中强调了能够根据手段和目的来规定的行为。(而且,按照这种观点,“理性的”就不是涉及诸如自由或正义这样的广义哲学概念,而是涉及人们怎样才能有效地完成组织的工作。)有了这种强调,理性模式就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人的一致的、可程序化的、有组织的思维活动上”,这个模式“首先关注的是与目标有关的行为”,并且“不问来龙去脉地设定了目标”(Argyris 1973,261)。
这样一种观点不承认广泛的人类经验,不承认人们有本能行为的事实,不承认人们在其生活中会经历混乱和不可预见性,并且不承认人们会按照远非理性的感情和情绪行事。此外,由于人的成长并不是一个充分理性的过程,所以建立在这种模式基础之上的组织就不会支持个人的成长、发展和“自我实现”。相反,这种理性模式倒是会十分偏爱那些将会改进组织理性的变化。那些变化很可能会十分保守,进而它们会因其“对事实的关注胜过对可能性的关注”而强化现状(Argyris 1973,261)。与这种观点相比较,阿吉利斯极力主张更加关注“个人的品行、真实性,以及人的自我实现”,更加关注与“企业的人性方面”有关的品质。
在公共行政领域,罗伯特·戈伦比威斯基对组织发展观(OD)进行了十分透彻的分析。在其早期的著作《人、管理与品行》(1967)中,罗伯特·戈伦比威斯基对传统的组织
全文共10733字,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411]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 通过在消费者心中树立品牌关系导向来提高酒店品牌绩效外文翻译资料
- “友好“抱怨行为:走向亲密的手段外文翻译资料
- 服务蓝图:针对关键服务流程的有效方法-在四星级国际酒店Arash Shahin 管理部进行案例研究外文翻译资料
- 组织中女性高管职业生涯规划与晋升的视角:连锁性别偏见的经验,双重束缚,和不成文的晋升规则外文翻译资料
- 影响优秀员工工作满意度的激励因素识别外文翻译资料
- 探索离职意向的影响因素:以豪华酒店员工为例外文翻译资料
-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酒店旅游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外文翻译资料
- 酒店Twitter账号的营销效果:以沙特阿拉伯为例外文翻译资料
- 酒店旅游市场营销外文翻译资料
- 中国经济型酒店SWOT分析外文翻译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