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治的理由吗?中国社区的土地所有权和民主参与
Sally Sargeson
摘要:土地所有权的变动是否影响人民的民主参与?关于这一主题的定量的、跨国家的研究由于管理制度和文化的不可比性,以及使用粗糙的指标来确定参与程度而受到影响。本研究试图克服这些方法上的问题,通过使用程序性和实质性参与的指标,对来自中国的五个地点的定性数据进行结构性的历时比较。中国是一个威权国家,但它要求城市社区和村庄的居民参与“自治”。它考察了土地从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国家所有制,以及居民有偿获得现金和安全、可替代资产,是否以及为什么会增强或削弱自治的参与。在研究中发现,集体土地所有权促进了自治的参与。土地转为国有和人民对私有财产的占有削弱了参与性。研究的有力结果支持了一个因果论证的方向,即集体土地所有权有利于民主参与。这些发现表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改变土地所有权可能带来的负面政治后果。进一步的暗示是,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一个城市化的中国可能在社区层面上不够民主,而不是更民主。
关键词: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财产;征用;民主;选举;村庄;城市社区;城市化
介绍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明确界定、确保个人财产权的安全,激励所有者利用民主制度保护自己的财富,免受独裁者的掠夺(Ansell和Samuels 2010;托克维尔2007,367-69)。一些学者也认为相反的观点是正确的:集体的、不可分割的财产既没有给人们激励,也没有给他们必要的制度和组织资源来选择如何治理和由谁治理。
类似的批评也针对中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尽管批评者通常认为,集体所有制产生的经济效率低下使得农村土地所有权、证券化和私有化成为必要(Deininger et al. 2013);然而,参见Zhang和Donaldson 2013年的研究报告),向“不确定的、可继承的和可转让的土地个人产权”的转变也被提倡作为提高人民自治参与的一种手段(世界银行和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142;参见Qin 2007;于2008年)。
土地所有权的变动是否影响人民群众参与基层自治?虽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对政治理论和体制设计具有重要意义,但迄今为止对发展中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如何影响人民政治参与的详细比较研究很少。在中国,没有什么问题比这个问题更紧迫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市扩张征地速度,以及正在进行的个人财产权登记试点,都有可能使集体土地所有权脱离农村和社区自治机构。这是中国人民直接选举领导人、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的唯一政府领域。在农村和社区层面上,中国无疑是专制的。然而,在中国,对于土地所有权的变化是否以及如何改变人们对这些单一自治领域的参与,也知之甚少。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浙江省5个地级市定性数据的结构化、历时性比较,分析了土地所有权的变化是否增强或削弱了自治的参与。研究发现,在研究场地中,集体土地所有权有利于更高层次的程序民主和自治的实质性参与。相反,土地的征用和向国家所有权的转变,以及前业主对现金和其他资产的补偿性取得,削弱了以前参与自治的人民的参与。这些发现与自由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假设相矛盾。本文的结论部分探讨了本研究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将财产所有权理论化为促进民主参与的因素
由于财产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Alexander and Penalver 2010),有必要认真思考什么样的财产制度和资产类型最有利于公民的民主参与。支撑这种启发式方法锻炼,我利用达尔的建议(1998年、91年- 93年),一些标准定义一个国家民主(比如一个独立的媒体和多党竞争)可能会放松当评估小型社区的民主状况直接选举领导人和成员,在包容性协商论坛,决策影响他们的社区。因此,如果所有成年人都在定期、相对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中投票给他们的领导人,并有机会提出、获得关于政策选择的信息和辩论,并决定如何治理他们的社区,那么参与社区自治就被理解为包括民主参与(della Porta 2013, 40;Pateman 1970 2)。
自由主义理论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个人对财产的私有制推动了民主化。他们声称,民主保障措施是由理性的公民创建并使用的,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富不被独裁者征用或任意征税(利普塞特1959年;摩尔1966)。由于个人财产所有权不断地激励人们参与自治,Singer认为授予所有者的权力最终会受制于通过民主程序达成的规则(2014,1328)。通过一个良性循环,私有财产法因此成为民主的基石之一:一个准宪法框架,支持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事实上,自由主义的信念是如此坚定,有房业主更喜欢民主,以至于直到20世纪90年代,实证研究有时使用民主制度作为私有财产的代理(Leblang 1996, 5;参见Boix和Stokes 2003;奥尔森在1993年,572年)。
对于私有财产是民主基石的自由主义假设,现代化理论家将城市化作为一种干预的因果机制。华莱士(2013)认为,城市的集中有利于业主为保护其物质利益而采取的集体政治行动。Hicken(2007)阐述了这一论点,他的理由是,不仅在城市建立民主的集体努力比在农村更有可能,而且城市民主更强大,因为居民更高的收入、法律知识、沟通和组织技能使得购买选票的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却步。
然而,对自由主义假设的实证研究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并产生了非结论性的结果。例如,Russett的早期研究(1964年)比较了不同的监管体系和文化,并将选举作为民主参与的粗略指标。除了布恩对几个非洲国家土地保有制度的政治后果所作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比较分析之外,支持自由主义假设的证据有限。而且,尽管Boone确实发现土地私有化促进了公民民主权利的扩展,从而扩大了对国家政治的参与,但她也得出结论,公共土地制度可以激励参与,从而加强拥有土地社区成员的政治权利(2007,577)。
把城市化和民主化联系起来的现代化论点也没有经受住批评的审视。人们对民主参与的偏好和能力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没有发现差异。例如,在对100多个国家的小组研究的基础上,一旦收入保持不变,Barro(1999)发现没有证据表明更高的城市化导致更大的民主。现代化的论点也与自由主义的推理不一致,自由主义的推理认为,征用的威胁,以及业主因此对其财产的民主保护的要求,可能会因资产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土地的供给是固定的,难以隐藏,而货币、消费品和住房的供给是有弹性的,这些资产的所有权更容易隐藏(Adsera, Boix, and Payne 2003, 460;Ansell and Samuels 2010, 1544)。由此得出的逻辑推论是,由于自耕农依靠土地为生,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要求民主(Russett 1964;威廉姆森2009)。
最近对中国的研究为这些现代化和自由主义理论提出了一个难题。首先,与现代化理论相反,中国城市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意愿似乎低于农村居民。当然,正如自由主义理论家所预测的那样,城市房主会为保护自己的财产而战。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他们通过请愿、诉讼和抗议来保卫自己的家园(Gui,Cheng, and Ma 2006;读2012年,73 - 78;而不是利用社区自治的机构和机关。事实上,城市社区选举的程序质量和民众参与决策的水平低于乡村(阅读2012,73),社区自治组织成员通常充当上级政府的代理人,而不是居民代表(Heberer 2009)。
其次,村民不仅比城市居民更多地参与自治,而且在农业领域的参与似乎更强(Huang 2014, 287-88;Kennedy 2010, 183;Oi和Rozelle 2000;舒伯特和阿勒斯2012;小王和Yao2007)。以往村级选举的程序质量越高,后续选举的投票率就越高,当选的领导人对选民的要求而不是政府的指示做出的反应也越多(Kennedy 2010;Kung, Cai,和Sun2009;Su等,2011)。然而,与自由主义的逻辑相反,中国的农田不是由个人所有,而是由集体所有。
然而,在这一点上,学者们忽略了来自中国的异常证据所带来的理论难题。也没有调查明显的经验性难题:尽管最近的研究提供了城市和农村社区的财产制度和政治参与的快照,但很少有人研究了土地所有权和城市转型社区的政治参与之间的动态互动。本研究通过对同时期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实证比较,分析在这些社区中,随着土地所有权的改变和村民的城市化,人们参与自治的程度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从而应对这些挑战。为了为这种比较铺平道路,下面的章节将解释中国立法中土地和自治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城乡差距:土地所有权与自治
我国《宪法》(1982年,2004年修订)、《土地管理法》(1998年,2004年修订)和《物权法》(2007年修订)将土地所有权分为两类。城市居民点、矿山和国家基础设施占用的土地全部为国有。1988年以后,立法改革开放了城市国有土地长期租赁市场。随着2007年《物权法》的通过,保障住宅用地租赁期届满自动续期,加强了住宅用地租赁期的安全性。Clarke(2014)认为,城市国有土地租赁附带的权利现在类似于私人所有权。物权法还加强了在城市租赁土地上建造公寓的所有权。到本世纪初,城市房地产的所有权相对安全、可替代,而且——正如不断上涨的价格所证明的那样——价值极高(Deininger and Jin 2009)。
农村土地由有领土限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的成员共同所有。在法律上,集体成员(村民)的所有权由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行使。从这些委员会中,农户可以承包集体耕地30年、林地70年的使用权,并购买建设房屋用地的长期使用权。自1999年以来,承包者的耕地使用权得到加强。在合同期间,承包商可以转租、转让、遗赠土地,并越来越多地将其使用权抵押给农田(但不包括宅基地)。村委会还将未使用的集体土地整理出租给外地承租人。通常,土地是村庄集体拥有的最有价值的资产(通常也是唯一的)。
但是,法律禁止集体所有的土地转让,禁止擅自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除部分试点地区外,集体土地由政府征收转为国有是农村土地进入城市黄金房地产市场的唯一合法途径。集体土地被征用时,政府和企业必须赔偿集体所有人的土地损失,并支付集体成员的安置和社会保障费用。土地承包者、承租人和房屋所有人分别获得补偿,以补偿损失作物的重置价值、多年的承包和租赁土地使用权以及建筑物。批评者认为,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对集体所有土地转让和开发的监管限制降低了村民土地权利和房屋所有权的安全性、可替代性和价值(Prosterman et al. 2009)。
中国的村庄和城市社区都被称为“自治”。从法律上讲,他们必须进行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所有符合条件的成年居民都可以提名和投票给村委会和城市社区委员会的候选人,尽管省级执行条例通常要求候选人忠于党的,不违反法律和政策。候选人的人数必须超过当选的办公室职位的人数。选票由政府批准印制。投票是秘密的,投票是公开统计的,选举结果会立即公布。为了在每三年一次的选举和每年一次的集会之间代表他们的利益,村庄小团体和城市街区的成员应按比例选出代表,代表他们在与当选的村庄和社区委员会的会议上采取行动。在法律上,如果不总是在实践中,选民可以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和直接参加议会,审查、修改和否决委员会的决定,并罢免委员会成员。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法律为城市和农村社区的民主参与提供了制度框架和空间(Heberer 2009, 503;O #39;Brien and Han 2009)
然而,城市(国家)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立法分离使城市和农村委员会的职能和财政资源有所不同。当然,这两个委员会的许多职能都是世界各地地方议会的主要职责:管理地方基础设施、拒绝和发放许可证、处理居民的记录和福利申请、处理他们的投诉以及调解他们之间的争端。其他功能,如监控繁殖,是中国独有的。但除了这些作用之外,《村组织法》还要求村委会管理集体资产和收入。在执行这些管理任务之前——例如,花费集体资金;申请贷款或项目资助;征用劳动力;分配宅基地、土地使用合同和租赁;支出或者发放土地补偿款;或者为非“核心”委员会成员设定工资——村委会必须得到村委会或村民代表的多数同意。此外,他们必须公布经选举产生的乡村审计组和市镇当局批准的季度账目。
相比之下,城市社区通常位于国有土地上。虽然社区委员会在法律上被授权“管理社区委员会的财产”,但大多数社区委员会不拥有财产,不参与管理居民的财产,也没有独立的收入来源。相反,他们从病区政府那里收到了详细的预算。这些预算通常仅够支付委员会成员的工资和办公室开支(Tomba 2014, 46 - 7,83 - 84;参见Heberer 2009, 504)。因此,城市委员会在支出方面几乎没有自主权。
除了这些民选委员会外,中国几乎每一个乡村和城市社区都有一个当地的共产党支部,支部的成员选举一个党委,党委又选举一个书记。早期的研究有时将党和选举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种敌对的、零和的权力竞争(郭和伯恩斯坦,2004)。但是,基层党代会与选举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党委完全纳入和同时担任选举委员会的全部职务,到鼓励竞争性选举和与选举产生的负责人合作的党委,有14个。我自己的研究网站提供的证据支持Sun等人(2013)的观点,即村党支部正在向他们的委员会和书记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对党和村选民做出更积极的反应。
研究地点及方法
在中国,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时,人们对自治的参与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缺乏经验证据来回答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所有权形式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粗略的民主程序指标和在一个时间点收集的大n数据集来检验的,这些方法是测量相关性的理想方法,但不能确定因果机制和途径(Gerring 2009103)。
系统地比较少数案例内部和跨少数案例的过程是一种更有效的方法,可以识别因果机制,并证明内部有效性(Hall 2008)。根据班纳特和Elman (2006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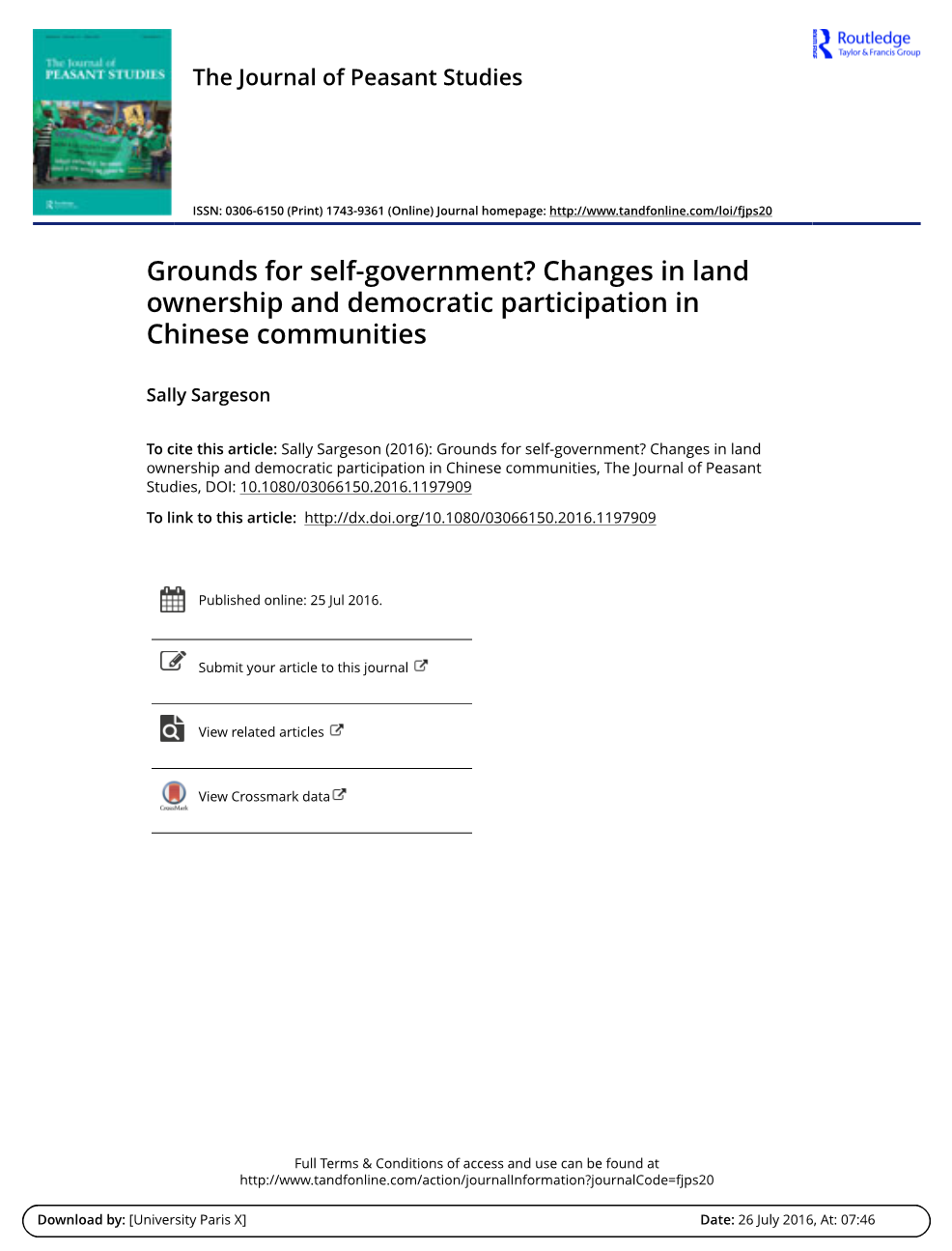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27 页
资料编号:[4732]


